夏志清教授逝世的消息傳來,我並不驚愕,只祝他一路好走,平平安安地到另一個世界,沒有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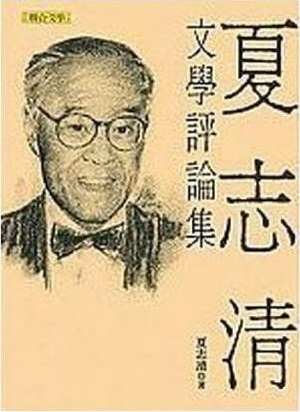
夏公(我們學生輩的人都這樣稱呼他)名震遐邇,在華人文學世界,無人不曉,寫追悼文章的人士當然也不會少。但我知道夏公在天之靈是不喜歡歌功頌德式的應景文章的,所以只能從我個人近年來和夏公交往的經驗和感受講起。
記得最後一次去紐約拜訪夏公,已經是四五年的事了。當時因返美公幹,路經紐約,我妻李子玉建議去看夏公。我怕他年歲已高,不便打擾,但又覺機會難得,所以約好某日下午去看他。我們準時到達,開門的是夏公自己(師母王洞剛好到中國大陸旅遊),他一眼見到子玉,就冒出一個字:Natasha!我們一時呆住了,進得門來,他就滔滔不絕地和我大談俄國小說,原來指的就是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的女主人翁。
熟悉夏公待人接物的一貫作風的朋友都知道,他不管是新交或舊知,一見面就直言無忌|| 也有人說這是夏公返老還童,「童言無忌」,對年輕女性甚至會「動手動腳」,我妻初見他時果然如此,但她並不介意,反而覺得這個老人很率直。作為學生輩的我在夏公面前一向靦覥,那一天也沒有例外,靦覥之餘只好以嚴肅誠懇的語氣向他求教。偏偏我自從讀研究院起就酷愛俄國思想史和俄國小說,於是很自然地和他攀談起來。夏公說他最近重讀俄國文學經典名著,覺得實在了不起,世界沒有任何國家的小說|| 包括中國小說|| 可以比得上,如果勉強再作比較的話,他說只有Middlemarch(George Eliot)或可與托翁和杜翁(杜斯陀也夫斯基)相提並論。我自己招認還沒有讀過這本英國小說,夏公迫不及待地訓誡說:「趕快看!真是了不起!連Della(師母的英文名)在我的影響下都讀過了。」
我回港後立刻買了一本此書的紙面版,厚厚的一冊。可惜的是,至今還沒有得閒讀。倒是把《戰爭與和平》的新版英譯本讀了一遍,感受良深。
如何成為現代文學的主流
回味那一天和夏公的談話,終於了解他的看法。幾十年來夏公對文學的價值堅持自己一貫的立場:最好的文學作品,必須能夠探索生命的意義和最基本的道德價值,也因此更能把人的善惡刻劃入微。這不但需要文學技巧,而且作家本人更需要勇氣。夏公認為,十九世紀的俄國小說比中國現代小說深刻多了,沒有人寫得過托爾斯泰和杜斯陀也夫斯基。「還有契訶夫!」我記得在夏公面前斗膽加了一句,他不置可否。
那麼魯迅呢?還有他推崇的張愛玲,她是否也有此深度?在此暫且不表,因為談夏公對這兩位作家的評價的人太多了,我不願囉嗦,先「缺席」不論。只想補充一點看法:夏公有一篇討論中國現代文學的名文,題曰「Obsession with China」,老友劉紹銘將之譯成「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有畫龍點睛之妙。研究或關心中國文學的朋友,都覺得夏公一語中的,把中國現代作家的特別情操點出來了,而中國小說有此特色,乃天經地道。我認為夏公的批評視野不止於此,他在文中雖然讚賞不少晚清和五四時期的作家,但也特別指出與現代西方不相似的地方:「中國愛國志士所夢寐以求的理想,也是現代西方文明所以追求的理想,但是,西洋文學的代表作品卻對西方文明的成就棄如敝屣,而着重描寫個人精神上的空虛,站在現代文學的立場,來攻擊現代社會。」(見夏公著:《愛情.社會.小說》,頁81)他引用的參考理論是當年美國名批評家屈林(Lionel Trilling)的一篇文章:〈論現代文學的特色〉(On the Modern Element in Modern Literature)。如用當今的西方理論加以衍義,就是說西方現代作家對於「現代性」(Modernity)的失望和幻滅,而用文學手法來批評。中國現代作家批評的僅限於中國社會的陰暗面,這是一種歷史造成的局限,所以夏公在文中說:「假使他們(指中國作家)能獨具慧眼,以無比的勇氣,把中國的困境,喻為現代人的病態,則他們的作品,或許能在現代文學的主流中,佔一席地位。」(頁83)
夏公這一段話,語重心長,也需要一種道德的勇氣,因為中國不少熱愛祖國人士會罵他沒有民族感情或政治偏見太深。多年來對於他的名著《現代中國小說史》的批評,也多從這個中國人的立場出發,而沒有正視他在書中大量引用作為比較的西方文學作品。
從「新批評」發現什麼
夏公畢竟是研究西方文學出身的,他在耶魯攻讀的是英國文學,師從當年「新批評」的幾位大師,他最推崇的一本小說理論書是英國F.R. Leavis的The Great Tradition,這位教授獨排眾議,把他自認為最重要的五位英國現代小說(Austin, Eliot, James, Conrad, Lawrence)一一列出,推到經典名著的地位。夏公採用同一種筆法,堅持他自己的文學標準。一九六一年夏公此書的英文原著初出版時,美國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人幾乎人手一冊,我初讀過也覺得他不免有偏見之處,但無損其學術分析的精闢。經過半個世紀以後重讀,更感到這些政治偏見並不重要了。時過境遷,所有的文學作品之能夠傳世,都靠它們本身的文學價值。夏公所堅持的是一種文學的「世界觀」|| 也就是說,把感時憂國的精神從寫實的狹意範圍提昇到人類全體的視野,所以夏公在文中說:表面看來,現代中國作家「同樣注視人的精神面貌,但英、美、法、德和部分蘇聯作家(按:指的是寫《齊瓦哥醫生》的Pasternak)把國家的病態,擬為現代世界的病態。」(頁82)
當今的「後現代」世界的病態實在太多了,然而當代西方文學本身卻顯得有氣無力。我發現自己和夏公一樣,從重讀文學經典中求得精神上的救贖,「感時憂國」已經不夠用了。受到那一天和夏公一席談的感召,我非但讀了托翁的《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而且重讀當年影響我至巨的杜翁小說《卡拉瑪佐夫兄弟》,又開始讀另一部更黑暗的《群鬼》(Demons,又名The Possessed),甚至約有心讀者開讀書班一起讀。
俄國小說是否屬於西方現代小說的一部分?夏公可能認為理所當然,因為當時歐洲的作家都看俄國小說(當然是譯本),反之亦然。我從英文譯本得到的感受是:即使讀的是英文,但托翁和杜翁的小說世界描寫的依然是道道地地的俄國,他們都是「感時憂國」的作家和知識分子,卻能在小說中把歐洲的文化價值納入他們的文學,並作批判,在「憂國」之餘,所探討的是整個現代文明的危機。這一個偉大傳統,在俄國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政治掛帥「蘇聯文學」後又復蘇了,甚至可以說從來沒有真正斷過。《齊瓦哥醫生》先以手抄本在地下流行,後來才被偷運到意大利除英譯版,可惜譯文太差,最近又有新譯本,和托翁 、杜翁的經典一樣,歷久不衰。
珍惜日常生活的意義
在夏公影響之下,我已經放棄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專家」的角色,逼自己進入「世界文學」的領域。這才發現,自己早該讀卻沒有時間讀的西方文學經典實在太多了,甚至連歐洲現代小說的始祖《唐吉訶德》也沒有讀過。夏公在耶魯作研究生,甚至在上海滬江大學念書的時代,已經和乃兄夏濟安教授|| 我在台大的業師|| 遍讀西方經典,在他們來往的書信中可見其端倪。我個人在學術上的路數|| 特別是對於魯迅的研究|| 較接近濟安師,可惜他英年早逝,從來沒有和我談過俄國文學。濟安師過世後,他的學生都自動轉到夏公門下。妙的是,每次和志清師見面,我們談的大多和中國文學無關,不是聊老電影(夏公對此如數家珍,特別喜歡劉別謙(Ernest Lubitsch)的作品),就是談西方文學。這一段文學因緣,令我銘記在心,至今難忘。
近年來,每到聖誕節子玉必會寫信問候,他也必回,他的回信中時時不忘祝福我們的婚姻,讓我終於領悟到那一天他突然叫出Natasha這個名字的背後深意:當時還以為他讚賞子玉看來天真年輕,有點像托翁名著中的女主角,但其實夏公在講他的讀書心得:托翁在小說中更關心的是人婚姻和家庭的意義,連一場拿破崙征俄的大戰,也終歸煙消雲散,反而不見得比Pierre和Natasha的婚姻和家庭幸福更持久。現在我也進入老年,更珍惜日常生活的意義,它是人生必經的過程,也是人性的一面,更是人類的普世價值之一。托翁小說之所以耐讀,就在於此。但願夏公在天之靈聽到我這一番天真的「告解」之後,會哈哈大笑。
(原刊載於明報)

Be th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