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文革後48年,一名頭髮灰白的女士來到北京師大女附中(現稱師大附屬實驗中學),讀出1500百字懺悔書,向文革時被逼害的師生致歉,她說,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終身面對的日子。
她的名字叫宋彬彬,中共元老之一宋任窮的女兒,文革時期是高中三年級學生、共產黨員、該校革命師生代表會副主任和紅衛兵首領,她最為人熟悉,就是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她以代表身份給毛澤東獻上紅衛兵袖章,當時毛知道她的名字源於「文質彬彬」四個字後說了句:「要武嘛」,從此,全國上下不愛紅妝愛武裝,暴力狂潮掀起,殺戮此起彼落。毛的「要武」論廣傳後,單是北京市就有1772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當中包括很多老師和校長。
其實,早在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走紅前的13天,一場殺戮已在她麾下的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隊上演了。
1966年8月5日,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發起「打黑幫」活動,很多學生都湊興來參加,她們抓來三個副校長和兩個教導主任,先往五人衣服上倒墨汁、戴高帽,在脖子上掛牌子、用帶釘子的棒打他們、用鍋爐房剛煮沸的開水燙他們,強迫他們挑重物……經過三小時折磨,第一副校長卞仲耘受不了昏倒地上,此時她已遍體鱗傷、大小便失禁、瞳孔擴散,處於瀕死狀態。學生卻把她丟進垃圾車,五小時後才有人發現把她推到醫院,可惜抵院已證實她死亡多時。
於是,卞仲耘副校長便成了文革中死在學生手下的第一位老師,此後,這類學生鬥死鬥傷師長的慘劇陸續有來。
當暴力被「正名」、或被合理化、甚至美化,要糾正、收回,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潛藏的惡魔跑了出來,人就會成為禽獸。卞副校長被她教育出來的學生一拳一腳打死,揮拳出腿的都是年輕少女,如此所為需要的不是勇武、力度,而是獸性。
十年文革,把一代年輕人的獸性釋放出來;香港79日佔領中環的後遺症也一樣,黃傘兵對不同顏色陣營的恨、對陌生人無緣無故的惡,除了獸性,沒法解釋。至於滅絕獸心要多久才能變回惻隱人心,以宋彬彬公開道歉的經驗來說,是48年。
所以,當很多人以為雨傘暴動陰霾已過,那是太樂觀了,看兩個月前香港大學學生對付李國章、盧寵茂兩位教授時的張牙舞爪,我想,如果當時沒有護衛、如果當時無人擋駕,兩位教授的下場,隨時跟師大女附中的卞仲耘副校沒兩樣。
當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發號施令叫示威者衝入公民廣場,當「佔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聲嘶力歇叫市民公民抗命,當港大學生會會長理直氣壯叫學生「以武抗暴」,效果就如同當年毛澤東那句「要武呀」,把犯罪行為美化,把罪惡感壓抑,以理想砌出貞節牌坊,擋住所有執法的路。雨傘暴動的最大禍害,就是釋放了人心的惡魔。
細心觀察,這年來,大家粗言多了,憤懣多了,看不過眼的事也多了;這年來,社會價值觀倒塌,道德敗壞,尊卑失了,尊重沒了。這一年,香港人心糜爛,如同當年文革。
黃傘兵依然拒認自己是紅衛兵,原因有二,一是因為他們根本不認識文革;二是他們認為文革是一場大洗腦,被洗腦者,如同嗑藥,成了一班舉著小紅書的喪屍,跟他們今日追求民主自由不可同日而語。
我想大家冷靜回想,雨傘暴動的日子,無論畢業也好、頒獎也好、講座也好、上課也好、爬山也好……總有人室內打起黃傘,或者扯起黃幡,如同嗑藥喪屍,喃喃唸著「我要真普選」。那黃傘黃幡就像當年的毛語錄小紅書,是革命靈符,高舉了,就什麼道理都不用說,什麼話也聽不進耳。其實傘兵一樣被洗了腦,他們信奉的是民主邪教。
還想一提,是那位紅衛兵頭目宋彬彬的下場。投身屍橫遍野的文化大革命,紅了的領頭人事後沒有被控告、問責,反而在1980年赴美留學,並取得美國國籍,從此定居美國,在環保局工作。
對黃傘兵投鼠忌器地仁慈
今日香港的雨傘暴動領導者無一受刑、無一被控、無一認罪、無一承擔,一個個像宋彬彬那樣若無其事逍遙法外,如果,政府、執法者和司法界繼續對黃傘兵投鼠忌器地仁慈,那就是對守法市民的集體欺凌,我們不要等48年後的懺悔,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頭戴民主光環的傘兵也例外不了。■
《亞洲週刊》2015年10月4日 第29卷 39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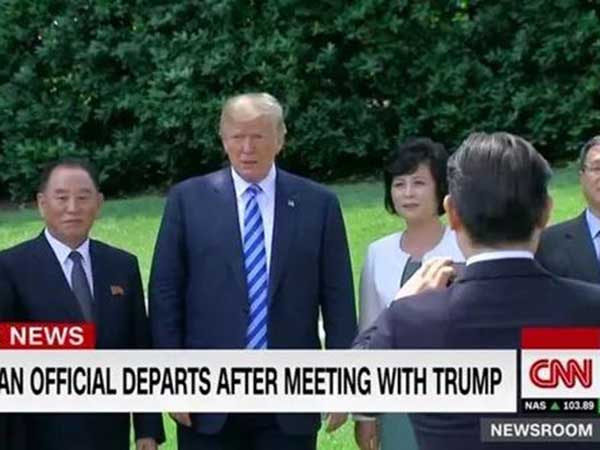


Be th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