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先生的這篇談中國詩,是1945年12月6日在上海對美國人的演講,主要講解了中國詩與西方詩在形式方面的不同以及對待中國詩歌以及中國詩歌研究的正確態度。既批評中國人由於某些幻覺而對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毫不留情地橫掃了西方人由於無知而以歐美文化為中心的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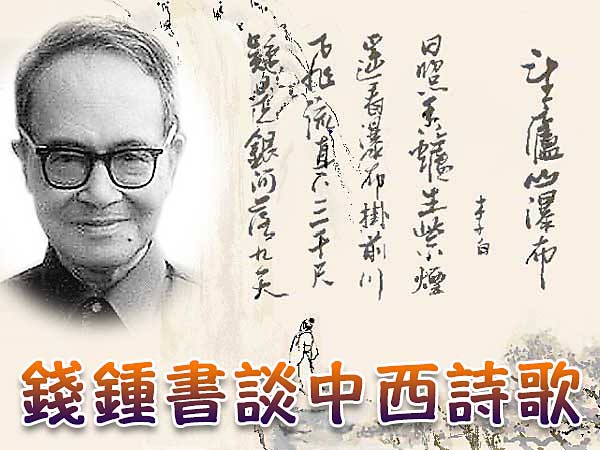
翻譯者的藝術曾被比於做媒者的刁滑,因為他把作者美麗半遮半露來引起你讀原文的慾望。這個譬喻可以移用在一個演講外國文學者的身上。他也只是個撮合的媒人,希望能夠造成莎士比亞所謂真心靈的結婚。他又像在語言的大宴會上偷了些殘羹冷炙,出來向聽眾誇張這筵席的豐盛,說:「你們也有機會飽嘗異味,只要你們肯努力去克服這巴貝爾塔的咒詛(The curse of the Babel)。」
諸位全知道《創世紀》里這個有名的故事。人類想建築一個吻雲刺天的高塔,而上帝呢,他不願意貴國紐約的摩天樓給那些蠻子搶先造了,所以咒詛到人類語言彼此阻格不通,無法合作。這個咒詛影響於文學最大。旁的藝術是超越國界的,它們所用的材料有普遍性,顏色、線條、音調都可以走遍世界各國而不須翻譯。最寡陋的中國人會愛聽外國音樂;最土氣的外國人會收中國繪畫和塑像。也許他們的鑒別並不到家,可是他們的快感是真正的。只有文學最深閉固拒,不肯把它的秘密逢人便告。某一種語言里產生的文學就給那語言限止了,封鎖了。某一國的詩學對於外國人總是本禁書,除非他精通該國語言。翻譯只像開水煮過的楊梅,不夠味道。當然意大利大詩人貝德拉克(Petrarch)不懂希臘文而酷愛希臘文學,寶藏着一本原文的《荷馬史詩》,玩古董也似的摩挲鑒賞。不過,有多少人會學他呢?
不幸得很,在一切死的,活的,還沒生出來的語言里,中國文怕是最難的。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從事文化工作的人里,文理不通者還那樣多。至少中文是難到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程度。有位批評家說,專學外國語言而不研究外國文學,好比向千金小姐求婚的人,結果只跟丫頭勾搭上了。中文可不是這樣輕賤的小蹄子。毋寧說它像十八世紀戲劇里所描寫的西班牙式老保姆(duenna),她緊緊地看管着小姐,一臉的難說話,把她的具有電氣冰箱效力的嚴冷,嚇退了那些浮浪的求婚少年,讓我從高諦愛(Gautier) 的中篇小說(Fortunio)里舉個例子來證明中文的難學。有一個風騷絕世的巴黎女郎在她愛人的口袋裡偷到一封中國公主給他的情書,便馬不停蹄地坐車拜訪法蘭西學院的漢學教授,請他翻譯。那位學者把這張紙顛倒縱橫地看,禿頭頂上的汗珠像清晨聖彼得教堂圓頂上的露水,最後道歉說:「中文共有八萬個字,我到現在只認識四萬字:這封信上的字恰在我沒有認識的四萬字裡面的。小姐,你另請高明吧。」說也奇怪,在十七世紀,偏有個叫約翰·韋伯(John Webb)的英國人,花了不少心思和氣力,要證實中文是人類原始的語言。可是中文裡並沒有亞當跟夏娃在天堂里所講體己話的記錄。
中國文學跟英美人好像有上天註定的姻緣,只就詩歌而論,這句話更可以成立。假使我的考據沒有錯,西洋文學批評里最早的中國詩討論,見於一五八九年出版的潑德能(George Puttenham)所選《詩學》(Art of Poesies) 。潑德能在當時英國文壇頗負聲望,他從一個到過遠東的意大利朋友那裡知道中國詩押韻,篇幅簡短,並且可安排成種種圖案形。他還譯了兩首中國的寶塔形詩作例,每句添一字的畫,塔形在譯文里也保持着——這不能不算是奇迹。在現代呢,貴國的龐特(Ezra Pound)先生大膽地把翻譯和創作融貫,根據中國詩的藍本來寫他自己的篇什,例如他的《契丹集》(Cathay)。更妙的是,第一首譯成中文的西洋近代詩是首美國詩——朗費羅的《人生頌》(A Psalm of Life)。這當然不是西洋詩的好樣品,可是最高尚的人物和東西是不容易出口的,有郎費羅那樣已經算夠體面了。這首《人生頌》先由英國公使威妥瑪譯為中國散文,然後由中國尚書董恂據每章寫成七絕一首,兩種譯本在《蕉軒隨錄》第十二卷里就看得見。所以遠在ABC國家軍事同盟之前,文藝女神早借一首小詩把中國人美國人英國人聯絡在一起了。
什麼是中國詩的一般印象呢?
發這個問題的人一定是位外國讀者,或者是位能欣賞外國詩的中國讀者。一個只讀中國詩的人決不會發生這個問題。他能辨別,他不能這樣籠統地概括。他要把每個詩人的特殊、個獨的美一一分辨出來。具有文學良心和鑒別力的人像嚴正的科學家一樣,避免泛論、概論這類高帽子、空頭大話。他會牢記詩人勃萊克的快語:「作概論就是傻瓜。」
假如一位只會欣賞本國詩的人要作概論,他至多就本國詩本身分成宗派或時期而說明彼此的特點。他不能對整個本國詩盡職,因為也沒法「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有居高臨遠的觀點。因此,說起中國詩的一般印象,意中就有外國人和外國詩在。這立場是比較文學的。
據有幾個文學史家的意見,詩的發展是先有史詩,次有戲劇詩,最後有抒情詩。中國詩可不然。中國沒有史詩,中國人缺乏伏爾所謂「史詩頭腦」,中國最好的戲劇詩,產生遠在最完美的抒情詩以後。純粹的抒情詩的精髓和峰極,在中國詩里出現得異常之早。
所以,中國詩是早熟的。早熟的代價是早衰。中國詩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後就缺乏變化,而且逐漸腐化。這種現象在中國文化里數見不鮮。譬如中國繪畫里,客觀寫真的技術還未發達,而早已有「印象派」「後印象派」那種「純粹畫」的作風;中國的邏輯極為簡陋,而辯證法的周到,足使黑格爾羨妒。中國人的心地里,沒有地心吸力那回事,一跳就高升上去。梵文的《百喻經》說一個印度愚人要住三層樓而不許匠人造底下兩層,中國的藝術和思想體構,往往是飄飄凌雲的空中樓閣,這因為中國人聰明,流毒無窮地聰明。
貴國愛倫· 坡主張詩的篇幅愈短愈妙,「長詩」這個名稱壓根兒是自相矛盾,最長的詩不能需要半點鐘以上的閱讀。他不懂中文,太可惜了。中國詩是文藝欣賞里的閃電戰,平均不過二三分鐘。比了西洋的中篇詩,中國長詩也只是聲韻裡面的輕鳶剪掠。當然,一篇詩里不許一字兩次押韻的禁律限制了中國詩的篇幅。可是,假如鞋子形成了腳,腳也形成了鞋子;詩體也許正是詩心的產物,適配詩心的需要。比着西洋的詩人,中國詩人只能算是櫻桃核跟二寸象牙方塊的雕刻者。不過,簡短的詩可以有悠遠的意味,收縮並不妨礙延長,彷彿我們要看得遠些,每把眉眼顰蹙。外國的短詩貴乎尖刻斬截。中國詩人要使你從「易盡」里望見了「無垠」。
一位中國詩人說:「言有盡而意無窮。」另一位詩人說:「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用最精細確定的形式來逗出不可名言、難於湊泊的境界,恰符合魏爾蘭論詩的條件:
那灰色的歌曲
空泛聯接着確切。
這就是一般西洋讀者所認為中國詩的特徵:富於暗示。我願意換個說法,說這是一種懷孕的靜默。說出來的話比不上不說出來的話,隻影射着說不出來的話。濟慈名句所謂:
聽得見的音樂真美,但那聽不見的更美。
我們的詩人也說,「此時無聲勝有聲」;又說,「解識無聲弦指妙」。有時候,他引誘你到語言文字的窮邊涯際,下面是深秘的靜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淡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有時他不了了之,引得你遙思遠悵:「美人卷珠簾,深坐顰蛾眉;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這「不知」得多撩人!中國詩用疑問語氣做結束的,比我所知道的西洋任何一詩來得多,這是極耐尋味的事實。試舉一個很普通的例子。西洋中世紀拉丁詩里有個「何處是」的公式,來慨嘆死亡的不饒恕人。英、法、德、意、俄、捷克各國詩都利用過這個公式,而最妙的,莫如維榮的《古美人歌》:每一句先問何處是西洋的西施、南威或王昭君、楊貴妃,然後結句道:「可是何處是去年的雪呢?」
巧得很,中國詩里這個公式的應用最多,例如:「壯士皆死盡。餘人安在哉?」「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同來玩月人何在,風景依稀似去年。…春去也,人何處?人去也,春何處?」莎士比亞的《第十二夜》里的公爵也許要說:
夠了。不再有了。就是有也不像從前那樣美了。
中國詩人呢,他們都像拜倫《哀希臘》般地問:
他們在何處?你在何處?
問而不答,以問為答,給你一個迴腸盪氣的沒有下落,吞言咽理的沒有下文。餘下的,像啥姆雷特臨死所說,餘下的只是靜默——深摯於涕淚和嘆息的靜默。
西洋讀者也覺得中國詩筆力輕淡,詞氣安和。我們也有厚重的詩,給情感、思戀和典故壓得腰彎背斷。可是中國詩的「比重」確低於西洋詩;好比蛛絲網之於鋼絲網。西洋詩的音調像樂隊合奏。而中國詩的音調比較單薄,只像吹着蘆管。這跟語言的本質有關,例如法國詩調就比不上英國和德國詩調的雄厚。而英國和德國詩調比了拉丁詩調的沉重,又見得輕了。何況中國古詩人對於叫囂和吶喊素來視為低品的。我們最豪放的狂歌比了你們的還是斯文;中國詩人狂得不過有凌風出塵的仙意。我造過aeromantic一個英文字來指示這種心理。你們的詩人狂起來可了不得!有拔木轉石的獸力和驚天動地的神威,中國詩絕不是貴國惠特曼所謂「野蠻犬吠」,而是文明人話,並且是談話。不是演講,像良心的聲音又靜又細——但有良心的人全聽得見,除非耳朵太聽慣了麥克風和無線電或者……
我有意對中國詩的內容忽略不講。中國詩跟西洋詩在內容上無甚差異;中國社交詩特別多,宗教詩幾乎沒有,如是而已。譬如田園詩—— 不是浪漫主義神秘地戀愛自然,而是古典主義的逍遙林下——有人認為是中國詩的特色。不過自從羅馬霍瑞斯《諷訓集》卷二第六首以後,跟中國田園詩同一型式的作品,在西洋詩卓然自成風會。又如下面兩節詩是公認為洋溢着中國特具的情調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我試舉兩首極普通的外國詩來比,第一是格雷《墓地哀歌》的首節:
晚鐘送終了這一天,
牛羊咻咻然徐度原野,
農夫倦步長道回家,
僅餘我與暮色平分此世界。
第二是歌德的《漫遊者的夜歌》:
微風收木末,
群動息山頭。
鳥眠靜不噪,
我亦欲歸休。
口吻情景和陶淵明、李太白相似得令人驚訝。中西詩不但內容常相同,並且作風也往往暗合。斯屈萊欠就說中國詩的安靜使他聯想起魏爾蘭的作風。我在別處也曾詳細說明貴國愛倫·坡的詩法所產生的純粹詩,我們詩里幾千年前早有了。
所以,你們講,中國詩並沒有特特別別「中國」的地方。中國詩只是詩,它該是詩,比它是「中國的」更重要。好比一個人,不管他是中國人,美國人,英國人,總是人。有種捲毛凹鼻子的哈巴狗兒,你們叫它「北京狗」,我們叫它「西洋狗」。《紅樓夢》的西洋花點子「哈巴狗兒」。這隻在西洋就充中國而在中國又算西洋的小畜生,該磨快牙齒,咬那些談中西本位文化的人。每逢這類人講到中國文藝或思想的特色等等,我們不可輕信,好比我們不上「本店十大特色」那種商業廣告的當一樣。
中國詩里有所謂「西洋的」品質,西洋詩里也有所謂「中國的」成分。在我們這兒是零碎的,薄弱的,到你們那兒發展得明朗圓滿。反過來也是一樣。因此,讀外國詩每有種他鄉忽遇故知的喜悅,會引導你回到本國詩。這事了不足奇。希臘神秘哲學家早說,人生不過是家居,出門,回家。我們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圖不過是靈魂的思家病,想找着一個人,一件事物。一處地位,容許我們的身心在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個安頓歸宿,彷彿病人上了床,浪蕩子回到家。出門旅行,目的還是要回家,否則不必牢記着旅途的印象。研究我們的詩准使諸位對本國的詩有更深的領會,正像諸位在中國的小住能增加諸位對本國的愛戀,覺得甜蜜的家鄉因遠征增添了甜蜜。■




Be th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