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夏,將有超過三十億人的目光聚焦在俄羅斯,關注地球上最重大的體育盛事。而如果到這一天,你仍然不知道為什麼世界盃(World Cup)會如此令人著迷,接下來的一個月,你將會得到答案。

世界盃(FIFA World Cup)毫無疑問是當今世界最重大的體育賽事。一個簡單的對比是,2014年全球有大約10.1億觀眾觀看了巴西世界盃決賽,那是2017年美國NFL超級碗(Super Bowl)觀眾人數的十倍,而兩年前里約奧運會開幕式的全球觀看人數也不到它的一半。今夏世界盃的32個參賽席位是從國際足聯的210個成員國當中決出,而聯合國(The United Nations)的成員國數量是193個。
而它吸引人的地方在於,一項已然成為全球產業機器的體育運動,仍然在某程度上代表著人類最純粹的一面。一個簡單遊戲投射出的人性與普世價值,仍然以一種其他事情無法企及的力量,連通著相互間差異巨大的種族、文化乃至性別。
足球運動最初來自工人群體,因此它的存在方式無可避免地帶著強烈的工薪階層式的規則與抱負。這是隊制運動,但個人同樣有充分的空間施展所長。它相對公平,無論你來自什麼樣的種族、背景,甚或具有怎樣的身體和性格特質,在同一套規則下,同一片場地上,都有可能實現自我。
當今世上最好的兩個球員,一個自幼家貧,一個從小離鄉;一個有堪稱完美的運動員體格,一個自小需要注射生長激素;一個張揚自我,一個內斂沉靜;但兩人始終難分高下,平分了近十年所有的年度世界最佳球員「金球獎」(The Ballon d’Or)。
更重要的是,他們為世界每一個貧民窟的小孩樹立著榜樣:從家鄉的碎石路到世界盃的聖殿,並非是那麼不可企及。
前橄欖球運動員、美國政客傑克·坎普(Jack Kemp)說,美式橄欖球是企業資本主義,足球則是社會主義。
三奪世界盃的球王貝利說,足球是「美麗的遊戲(The Beautiful Game)」。
國際足聯在2004年確認了足球起源於中國,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足球運動形式是英國人的功勞:他們在19世紀制定了第一部足球比賽規則——在那個時代,他們習慣在很多事情上為世界制定規則,而足球也被輸送到了英國人踏足的每一片大陸。
歷史上第一場國家隊比賽並非在真正意義上的兩國之間進行。1872年,英格蘭與蘇格蘭以0比0打平。不知道是否因為他們的足球文化先於其他國家起步而沒有對手,反正自此,英國一直沒有以聯合王國的身份參加國際足球賽事。在國際足聯和歐洲足聯(UEFA),不列顛分成了四支「國家隊」。
或許是歷史的必然,足球運動走向世界、全面開花的時代,也正好是取得政權獨立之後的前殖民地期望尋找自我的年代。如今的南美足球強國巴西、阿根廷、烏拉圭等等,在足球運動發展之中都不同程度地將踢足球的方式視作民族身份意識的彰顯,這種強烈的傾向很大程度上一直保留到現在。
第一屆世界盃於1930年在烏拉圭舉行,那是為了紀念該國立憲100週年。在歐洲普遍不願參與的背景下,南美球隊統治了首屆世界盃。決賽中烏拉圭以4-2擊敗鄰國阿根廷,當時他們甚至為決賽時用誰的球爭論了一番(最終的結果上半場先用烏拉圭的球,下半場用阿根廷的)。
從那裏開始,四年一度的世界盃至今已經舉辦完20屆(只有1942和1946年因「二戰」而停辦),當中經歷了從雷米金杯(雷米特杯)到大力神杯的換代,參賽球隊也從第一屆的13隊逐漸增加到如今的決賽圈32隊。
英格蘭直到1950年才第一次參加世界盃,並在1966年作為東道主贏得了至今唯一一次冠軍。他們在溫布利球場對陣聯邦德國的決賽上,吉奧夫·赫斯特(Geoff Hurst,靴斯)打進永載史冊的「問題球」——多年之後,電腦分析技術才最後證實那腳打在橫樑底下彈地而出的射門並沒有進。那一根橫樑至今仍安放在溫布利的博物館內。
英國足球名宿比爾·香克利(Sir Bill Shankly)爵士的名言:「足球無關生死,它重於生死。」
英國人到現在仍然視德國(而不是阿根廷)為他們在足球場上的最大死敵,緣由一直可以上溯到「一戰」。事實上,正是在那場戰爭中間的1915年聖誕節,英德軍人在雙方戰壕之間踢了人類歷史上其中一場最著名的足球比賽,至今仍被視為足球喚醒人類良知與善意的經典事例。
至於德國人,也曾憑借足球場上的勝利挽救自己的國家。1954年瑞士世界盃決賽,在伯爾尼的滂沱大雨中,穿著新款可拆卸鞋釘的球鞋,西德隊逆轉戰勝擁有當時世界最佳球員的匈牙利(大致相當於如今一支中游球隊要戰勝西班牙)奪得冠軍。這場後來被記作「伯爾尼奇蹟」的勝利,鼓舞了德國人從「二戰」的陰霾中走出。有說法指,足球在戰後日耳曼民族重新崛起中所起的作用不亞於奔馳汽車。
1954年之後的半個多世紀中,德國人又拿下了三次世界盃冠軍,最近一次是上一屆,在巴西!
而匈牙利的命運則在那一場比賽之後走向了另一端——那次輸球兩年後,匈牙利革命爆發,有人相信,正是那場世界盃比賽的慘痛落敗催化了民眾的情緒。
足球場上的事延伸場外並不是歷史中的罕見事情。薩爾瓦多與洪都拉斯曾因為一場比賽走向戰爭邊緣;哥倫比亞後衛在世界盃上將球誤踢進自家球門之後,回國就被槍殺。
在俄羅斯世界盃開幕前一周,以色列將對阿根廷的友誼賽安排在耶路撒冷,結果阿根廷隊在收到巴勒斯坦的威脅之後不得不取消比賽。
如果你是個全球主義者,大概會慶幸在比賽數據分析(多虧了美國人)和技戰術變革(多虧了一個荷蘭人和一個加泰羅尼亞人)的推動下,如今的國際足球比賽似乎不再像過去那樣強調彼此對立。
不過,各支國家代表隊的民族性格特質仍然鮮明到了可以有刻板印象的程度。比如德國人紀律嚴明、嚴謹計算並且執行起來冷酷無情;法國人隨性多變;烏拉圭人強悍險惡;非洲人自由奔放但又冒進無組織……西班牙人的表現曾經總是達不到預期,但是進入21世紀之後,他們捧起了世界盃,並且踢出了這個時代最漂亮的足球。
這一次沒有出線的意大利,足球歷史不時與醜聞扯上關係——他們的頭兩次世界盃冠軍(1934和1938年)都是在法西斯政權無所不用其極之下奪得,但與此同時,他們又往往是大賽上極具戰鬥力的球隊。有一半意大利人後裔、同樣經歷過獨裁政權的阿根廷,被認為擁有著類似的特質。
在世界盃上,沒有哪一支球隊像阿根廷這樣同時具備著神性與魔性。這一點在1986年四分之一決賽下半場的那5分鐘內展現得淋灕盡致——一個叫馬拉多納(Diego Maradona)的小子在用手打進英格蘭隊一球之後,又在英國人未回過神之前單槍匹馬地解決了他們整條後衛線,打入了經認證的20世紀最佳進球。
2018年,他們又有一個叫梅西(Leo Messi)的球王,阿根廷人就像期待馬拉多納的「神跡」一樣呼喚他,只不過梅西並不是在阿根廷長大。四年前他一手將球隊帶進了最後決賽,最後一球輸給整體更強的德國隊。梅西在賽後獲頒賽事最佳球員獎卻一臉呆滯的神情,成為了阿根廷人最近的一次世界盃回憶。
相比之下,他們的鄰國巴西則是世界盃上最成功的球隊。他們是唯一進入了每一屆世界盃決賽圈的球隊,奪冠的次數也最多(5次),並且看起來總是踢得最快樂的一隊。只是這種快樂並非沒有代價:他們兩次主辦世界盃,都在自己的國土上經歷最災難性的失敗。
四年前他們在半決賽以1-7輸給德國,是他們歷史上最大比分的失敗;不過更加令巴西人刻骨銘心的大概是上一次。1950年那場世界盃史上最著名的決賽,超過20萬人湧進當時為世界最大的馬拉卡納體育場。巴西人只需要一場平局就能捧得世界盃,連他們自己都相信這已經實現——決賽前,當地報紙甚至提前印出了巴西隊全體球員的合照,稱他們是「世界冠軍」。只有烏拉圭人不服。後來的傳說是烏拉圭隊長賽前在更衣室裏將那份報紙放在地上,帶領全隊一起向它撒尿……後來的一切成為了歷史,烏拉圭人以2-1擊敗巴西人,馬拉卡納一片死寂,甚至據說當時就有人從看台上跳下。
那是巴西人共同的國難記憶,據說當時10歲的貝利在家裏對父親說:「爸爸,不要傷心,我會替您把世界盃贏回來」……
這一切都將在2018年被續寫。在接下來這一個月,無論是在盧日尼基體育場還是在慕尼黑的酒吧,在里約街頭的大屏幕還是在東京某個臥室的手機前,都有人會隨著世界盃而哭笑、嘶喊。情侶可能因此結識或分手,也可能有人中大獎或破產。人類一切的高尚與不堪,都可能在這一個月裏找到微觀的縮影,讓數十億人體會各自人生裏將會經歷或不可能經歷的感受,直到下一個四年。
這是世界盃,它無關生死,卻令人如歷盡一切。■
轉載:BBC中文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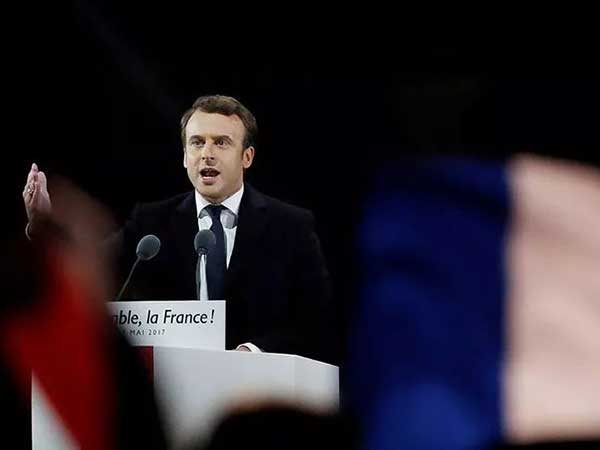


Be th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