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教育變了質,老師怕了學生,校長又怕了家長,自己都丟掉尊嚴,何來尊嚴的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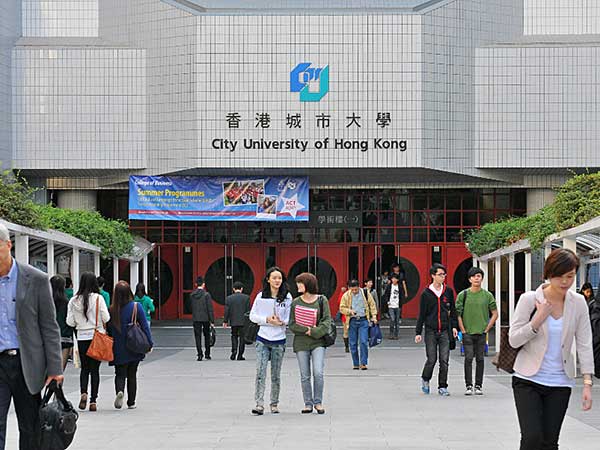
先說兩件陳年舊事……
唸書的時候,鄰座有個談得來的男同學,既多嘴又聰明,他很反斗(頑皮),老師說一句他反駁三句,常被罰,於是大家都把他標籤為壞學生。
有一天,男同學沒上學,自那天起,他消失了,有人說他退學,有人說他轉校,當年資訊沒那麼發達,大家也沒那麼八卦,漸漸地,忘卻此事,也忘了此人。
幾十年後,因為facebook,讓許多失聯的人都聯繫上,我目標較大,這男同學透過臉書找到我。幾十年不見,第一件事當然要解惑,原來當年他是因為聚眾打架被開除出校。他說,就是那一回,讓他對老師改觀。我以為,他從此痛恨一切教育……
「我在校務處門口親耳聽到訓導主任說,聚眾打架太嚴重,要報警!班主任苦苦哀求,叫主任趕我出校算了,千萬別報警,報警會毀我一生……我忽然驚覺,那個天天罵我罰我的老師,原來這麼疼惜我!離開後,我轉了幾家日校、夜校,最後勉強把書讀完,今日回頭,這半生,我最懷念的就是那個罰我罵我、最後還趕我出校的老師。經歷了人生,當上父親,才明白,那是教育。」
這同學因中途輟學,走的路比別人崎嶇,但今時今日,他比我們成功,最重要,是一直心懷感恩,沒半點怨恨。
另一個故事,是關於一宗校內「謀殺」事件。
我的中學訓導主任是個永遠板起臉孔的舊式教師,一天到晚在罵人,唯一見他展笑臉,是放學後在校園小池塘餵魚的時候。那一池錦鯉,是他多年心血。
訓導主任總是學校第一個出現、最後一個離開的人,我們知道他愛學校,也知道他緊張孩子,但沒人喜歡被罵,於是,很多學生怕他,更多學生憎恨他。
有一天,主任如常一早回校,發現整個池塘的魚死清光,他的心血,他的命根,一夜之間,煙消雲散,大家都猜到,是同學幹的,因為學校恨他的人實在太多。
這天,他一反常態,沒有罵人,倒是拿了個藍色汽油桶,把魚屍全裝進去,旁邊豎一塊黑板,上書:「一共九十六尾魚!」放在校門前,然後,自己搬一張椅子坐在旁邊,一言不發,在悼念。那個早上,每位上學的孩子走過校門,都心頭一凜,今日殺魚,明日殺人,誰家孩子,心腸如斯歹毒?我們彷彿聽到,主任的心在悲鳴。那天之後,我沒再見他養魚了。
我一直以為,罰人的老師最討人厭。長大後回望,年少時能給人狠狠地罰幾回,其實真是恩典。
風水輪流轉,我後來也當上教師,在浸會大學新聞系遇過幾個棘手學生。那幾個人不喜歡我的教法,專門跟我抬摃,我不留情面責備過他們,於是這幾個人開始逃我的課。
我的計分準則是出席率和課堂小測都會算進總分內,逃課者注定失分,學期尾算帳,他們的分數不是C-就是D。
問題來了,其中一個得C-的同學被我科的低分拖累,差零點一分拿不到獎學金,憤而向學校投訴。奇怪事來了,系主任、同事都來找我,問我可否把成績覆核多一遍,多給回他一兩分,好讓他能得回那獎學金。
明明錯的是他,到頭來要跪低(讓步)的是我?上司好言相勸,跟我剖析利弊:如果學生投訴,校方就要開個委員會徹查,你和我這暑假注定要泡湯……
我跟上司說:這個暑假,就給他,我奉陪到底。我是一分都不會動,那是他逃課的後果。他可以投訴我,他可以恨我,但二十年後,他就會明白,那零點一分,叫做教育。
教育,是細水長流,不爭朝夕的。學校應是教育的地方,不是誰怕誰的地方,但不知何時開始,香港的教育變了質,老師怕了學生,校長又怕了家長,自己都丟掉尊嚴,何來尊嚴做教育?
上星期,香港幾家大學都發生批鬥事件,中文大學懸著港獨旗、教育大學貼著嘲笑教育官員喪子的冷血字句,學校干預,學生群起攻之,中大學生更圍攻副校長,逼令他們就範,讓港獨旗繼續飄揚。
至於譴責學生的教大校長張仁良,迅速被網上起底,把他一家人的照片登了出來,兒子的名字和公司資料詳細列出。誰譴責我,誰的家人就遭殃,校長兒子也不例外。
姑息,自然養奸,別問為什麼今天大學生會變成這樣?想想我們社會何時開始對孩子連一個「錯」字都不敢說?大家只爭著當好人,說孩子喜歡聽的話,做孩子喜歡做的事。
我最近在電台節目訪問教育專家,發現一個怪現象,不少校長、社工都會稱頑皮學生做「比較有挑戰性的學生」,原來,因為怕標籤,連「頑皮」都叫不得了,那麼,一個「錯」字,是否該換成「有點不太對勁」呢?由一些富挑戰性的學生去做一些有點不太對勁的事,我們的世界,真的越來越富挑戰性和不對勁了。■
原文轉載自《亞洲週刊》2017年9月24日 第31卷 38期




Be th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