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行使了他的第一個總統否決權,駁回了國會參眾兩院關於終止其通過「緊急狀態」築牆的立法動議。特朗普姍姍來遲地行使否決權,其中倒是沒有太多講究,更構不成特朗普非典型總統權力的又一例證,反而完全得益於共和黨完全掌握白宮和國會兩院的第115屆國會的相對省心。類似的情況上一次正是克林頓,他也是在執政兩年後、等到金里奇等人奪回法槌之後才開始染指否決權。

雖然時間節點沒什麼講究,但否決本身還是大有政治文章:特朗普再次證明了在「移民局訴查德哈」案的底色上憑藉1976年《緊急狀態法》來糾正白宮完全是「與虎謀皮」般的徒勞(編註:1983年6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根據三權分立原則,在「移民局訴查德哈」案中判決美國國會行使了50年之久的立法否決權為違憲),但幾乎也是第一次看到了共和黨精英層內部的暗流湧動。出於各類不同考量,13位共和黨國會眾議員和12位共和黨國會參議員向白宮發難,讓外界直接聯想到特朗普能否維持黨內足夠穩固的支持。更為微妙的是,如北卡州國會參議員湯姆·蒂利斯或者科羅拉多州國會參議員科里·加德納等人迫於2020年連任壓力、不希望開罪於特朗普,竟然按耐住了此前表達的反對態度,但即便如此,還是出現了科羅拉多州第一大報《丹佛郵報》因極度失望而放棄對加德納背書的塌方式變化。這也意味着,特朗普在2020年面對的黨內精英與選民狀況並非那麼高枕無憂。
幾乎從他就任那一刻起,關於特朗普會否是「一屆總統」的疑問就被反覆拋出。這個在2020年大選前還不會有答案的問題對民主黨而言或許意味着寬慰與激勵,而對於大多數觀察者來說,卻更像是一條美國政治大戲連台、驚奇不斷的預告片。不過,時至今日,即便華裔候選人楊安澤可以神奇地擠過門檻、挺進前兩場辯論,大有時隔五十多年續寫民主黨版鄺友良傳奇的架勢(編註:鄺友良,美國首位華裔國會參議員,分別於1964年和1968年兩次參選美國總統選舉共和黨內初選),但2020年大選的這些「神奇」還是不足以撼動一些傳統,比如總統的在任者優勢。
總統是怎麼輸的?
美國總統是怎麼輸掉連任競選的?每當談及這個問題時,一個事實總會先被拿出來反覆強調,那就是特朗普的43位前任中只有10位未能成功連任,而且其中還包括了連任失敗、蟄伏四年之後又成為別人連任失敗理由的格洛弗·克利夫蘭(編註:格洛弗·克利夫蘭在1888年謀求連任失敗,1892年克利夫蘭再次參加競選,並擊敗共和黨候選人本傑明·哈里森第二次當選美國總統)。大概四分之一弱的比例體現了掌握行政資源的總統所享有的在任者優勢。
換一種算法,以五十年為單位倒敘,過去五十年中連任失敗者有三位,過去一百年中有五位,過去一百五十年中有七位,過去兩百年中有九位。甚至這10位連任失敗者之間的間隔年數(少則4年,多則48年)可以計算出的平均值為21年多,而2020年距離上一次老布殊連任失敗的1992年已過去了28年。這些歷史碎片或有或無地增加着2020年特朗普前景的撲朔迷離。
如果將1856年民主、共和兩黨首次同場角逐之前的三次失敗的連任歸結於政黨政治板塊快速且劇烈的衝撞,其後七位「一屆總統」的失敗教訓則可以依照某些邏輯收納分類起來。
首當其衝的規律應該還是總統選舉受到大環境或者大趨勢的累及。弗吉尼亞大學政治學教授拉里·薩巴托(Larry Sabato)在被問及在任總統連任失敗的原因時曾經感嘆道,「對最近的幾位『一屆總統』而言,與其說他們敗在個人弱點,還不如說更多是敗在局勢不利上」。其潛台詞是說,美國總統制下出現個人弱點突出到無法履職、必須撤換的情形並不多見,總統遭遇民意反彈的原因往往還是由於某些自身難保、失去控制的大勢所趨。
比如,赫伯特·胡佛在1932年的連任失敗當然是大蕭條的副產品,雖然小羅斯福的「新政聯盟」意味着對胡佛及其共和黨路線的徹底否定,但彼時指望着胡佛在一屆四年的任內力挽狂瀾、逆轉經濟周期,也一定是天方夜譚。再如,1976年卡特取代福特的結果,不一定預示着民意對共和黨失望,而是選民對尼克松及其「水門事件」的不滿殃及到福特的慣性趨勢。四年之後,卡特自己品嘗到的失敗,不但是在經濟失速、滯漲加劇以及能源危機甚至是「伊朗人質事件」的複雜背景下發生的,也被認為是跳脫共和黨周期四年後的註定回調。同理,1992年老布殊的惜敗不僅僅是克林頓口中的「笨蛋,是經濟」,還有民眾對共和黨白宮十二載或者列根「第三任期」的厭倦。當然,老布殊的例子也證明了「外交總統」或者「危機總統」難以避免的脆弱性:外交上的勝利永遠無法取代選民對國內經濟的天然關切。
如果說大趨勢是非戰之罪的話,在任總統連任失敗的一個致命阻礙當屬黨內分裂。這不但是作為本黨當然領袖的總統的最大尷尬,也是政黨「承重牆」在選舉中徹底瓦解的必然惡果。
最為戲劇性的例子,即1912年時任總統威廉·塔夫脫與同黨前任老羅斯福分別代表共和黨保守派和進步派的分庭抗禮。由於在稅收、勞工、司法等諸多領域的分歧,老羅斯福在離開白宮四年後再次出馬、在無法獲得黨內提名後竟然選擇自己組黨參選。於是,他的「麋鹿」進步黨以88張選舉人團票、27.4%的選民票在大選中位居第二,雖然比最終當選的民主黨的435張選舉人團票和41.8%的選民票存在距離,但也是美國歷史上在總統選舉中戰績最佳的第三黨了。值得玩味的是,即便是在共和黨如此生死攸關的分裂之下,塔夫脫還是拿到了23.2%的選民票,只是在選舉人團票意義上僅拿下了佛蒙特和猶他兩州的8票。
無論如何,1912年總統選舉的勝利者是坐收漁利的民主黨人,以及在難得的高光時刻發揮了正面作用的選舉人團制度。而要歸結共和黨的失敗的話,除了在自麥金利之後連續主政了16年的共和黨在面對新問題產生的政策分歧與路線之外,政黨機器和大佬們在總統候選人決定權上的主觀性一樣是鬧劇的根源:如果在1908年即老羅斯福為了堅持四年前不再謀求連任承諾而不參選的情況下,決定共和黨接替人選的不是老羅斯福自己,而是更多政黨精英的話,老羅斯福還要想在1912年單幹,估計只能靠梁靜茹給點「勇氣」了。
當然,即便黨內挑戰者最終被制度化地平息,其本身的參與也能說明不少問題。典型的例子是1976年在任總統福特在黨內遭遇的列根,或者在1980年在任者卡特在黨內遭遇的特德·肯尼迪。黨內湧現出強大的挑戰者,更多的是遠非無懈可擊的在任者自己發出的邀請。於是,在本黨初選起跑時就已然有一位虎視眈眈的強勢挑戰者的話,即便在任者可闖過提名關,在大選中估計也大概率地凶多吉少。
另外一個導致在任總統連任失敗的主要原因相對偶然,那就是選舉人團的扭曲。截止到2016年大選,美國歷史上已上演過五位選民票失利、但以選舉人團票勝出而當選的總統。不計入自己知趣放棄連任的拉瑟福特·海斯和還未嘗試連任與否的特朗普,其他三位總統中就有兩位連任失敗,這個比例幾乎三倍於美國總統制的總體水平。
這種回擺通俗講就是:即便可以藉助制度困境吞進去,四年後也還是要吐出來。而對於那個目前唯一第二次才贏得選民票的總統小布殊而言,很多研究認為,除了反恐戰爭作為單一主題的大背景之外,小布殊自身的定位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雖然他曾反覆強調自己是「團結者」(uniter)而非「分裂者」(divider),但按照威斯康星大學政治學教授巴里·伯登(Barry C. Burden)等人在2009年的研究,小布殊恰恰因為堅守了「分裂者」角色,進而定點而充分地動員到了更多共和黨選民,打破了所謂「中間選民決定論」的神話。
按照蓋洛普民調的數字,小布殊上任之初在共和黨內和全美公眾中的支持度分別為88%和57%,「911事件」之後這兩個數字同步上升為98%和90%。隨後,共和黨內部支持度的下降幅度遠低於全民支持度,在2004年大選前夕的最後一次民調中這兩個數字分別為93%和48%。由此可見,小布殊在「911事件」之後的很短時間中可能還是一個「團結者」,但很快就轉換成為了堅持反恐戰爭的「分裂者」,而這種選擇也直接拉高了保守派選民必要且關鍵的支持。
歷史經驗對特朗普意味着什麼?
美國總統連任失敗的歷史經驗雖然有限,但也還是可以為謀求連任的特朗普提供一些必要的參考指標,或者說給他劃出了一些大忌。
需要特別小心的問題是,未來兩年的美國國內與國際的大趨勢要如何加以利用。按照一般預期,美國經濟很有可能會在2019年第四季度或2020年初轉入放緩態勢。眾所周知,經濟上的負面變化一定對在任總統不利,何況還是長期以「某某指標創造了過去數十年乃至美國歷史上最好紀錄」之類句式來標榜自己功績的特朗普,更是將適任性和可選性直接綁在經濟績效上。但或許,經濟上的負面消息將給予特朗普的實際負面影響,未必如外界想象得那麼大。
一方面,無論是兩黨誰的功勞,特朗普上台以來的美國經濟態勢確實在持續向好,而選民對特朗普在處理經濟事務上的滿意度始終不低,這些完全不同於90多年前的經濟長期低迷以及胡佛因此而背負的極大民怨。另一方面,如今「人滿為患」的民主黨能否拿出一套可以迅速自證比特朗普(及其兩年具體執政)更為高明的經濟解決方案。這顯然是不太容易實現的任務,更何況在「小貝托時代」(編註:貝托指現年47歲、已參加2020大選的民主黨人貝托·歐洛克)的民主黨也很難想象再複製出一個小羅斯福精心打造的「新政聯盟」來。
即便未來兩年的經濟負面預期未必祭出致命一擊,國際舞台上的某些潛在引爆點正在某個拐點等待着發起夜襲。具體而言,眼下的朝鮮半島、伊朗甚至委內瑞拉等熱點在不同程度上都可能在2020年大選周期中搶光男主角的所有戲碼。
雖然在過去兩年之中,特朗普政府在相關議題的操作上所得相對微妙。在伊朗乃至中東事務上,特朗普對以色列的偏袒博得了美國國內福音派選民的心滿意足,且對伊朗強硬也是美國鷹派勢力的戰略審美要求,但某些撤軍或放棄責任的決定也在精英層中引發了頗多非議。在朝鮮半島事務上,各路民調雖然已能做出有半數左右美國民眾對特朗普處理半島事務表示滿意的積極結果,但同樣也有七成民眾壓根不相信特朗普所說的朝鮮已不是美國威脅的樂天派宣誓。
這也意味着,如果臨近選舉,某些熱點地區突然浮現出引發全美普通民眾關切的「危機」,特朗普又無力快刀斬亂麻式地擺平,其結果一定是拉低民眾對總統的信任度,甚至會誇大屆時民眾已有的關於經濟不景氣的怨氣。當然,外部壓力釋放藥效的關鍵是時間。如果「危機」被拖到大選日,絕大多數的結果是對在任者不利;如果「危機」在大選日之前化解,危機越大,反而對在任者越有利。從這個角度出發,特朗普如果要打那場傳說中每個美國總統都要打一下的仗的話,唯一的標準無疑就是奧巴馬的那句「不做傻事」,即節奏可控、杜絕泥潭。這可能也是特朗普政府目前對伊朗也只是極限施壓,「圖永遠不窮、匕始終不見」的一個原因。從這個角度再出發,原本就無法一蹴而就的半島事務,索性就慢慢談……如果可以在2020年的東京奧運會即距離大選日三個月左右之時在世界面前呈現出某些歷史性橋段的話,當然就是超級理想的輔選了。
在對國內外形勢戒急用忍的同時,特朗普也需要評估一下來自黨內的壓力到底有多大。這也是我們開頭提到的12位國會參議員倒戈背後隱含意圖的利害得失。當然,至少目前為止,共和黨內部還不太可能集結出一股公開與特朗普的「本土主義」針鋒相對的實權派力量,也很難湧現出如列根或甘迺迪那種實力派挑戰者。這對剛剛收編共和黨兩三年的特朗普而言已不容易,隱含的解釋或與共和黨的「特朗普化」或者特朗普獨大密切相關。
放眼猜想的話,如今還會被討論到的潛在挑戰者大概就是田納西州前國會參議員鮑勃·科克、馬里蘭州現任州長拉里·霍根或者俄亥俄州前州長約翰·卡西奇等人了。但這些人的存在乃至不時發表的一些反對特朗普的抱怨,更像是為共和黨傳統建制派留下的宣洩口和減壓閥,很難想象他們中的誰會對在任者特朗普發起強有力的挑戰。有趣的是,按照選舉造勢技巧的要求,特朗普身邊最好還是跟隨着一兩位陪跑者,以至於不要讓所有風頭都落到嬉笑怒罵的民主黨那邊。當然,其中的關鍵詞在於「陪跑」,不要太差,也不必多強。於是,已公開宣布參選、在黨內挑戰比自己小一歲的特朗普的馬薩諸塞州前州長比爾·韋爾德算是老有所為了。
那麼,特朗普會不會繼小布殊之後成為第二位連任時才獲得選民票多數的總統嗎?這可能才是特朗普真正要上心、解決好的大問題。雖然小布殊也被認為並非「團結者」,但他所製造的「分裂」還是與特朗普的大相徑庭。
在第一任期當中,小布殊的全民支持度因為「911事件」而一夜之間飆高,隨後三年中雖然處於穩步下降態勢,但在第一任期結束時只是回到了其上台之初的55%左右的水平。換言之,小布殊在提升黨內滿意度、擴展保守派選民的同時,其全民支持度在「911事件」的催化之下在第一任期之內大體維持、避免了斷崖式下降。但對如今的特朗普而言,過去兩年中的民調雖然穩定,但全民滿意度基本只能維持在30%到40%左右。如此穩卻低的民調也賦予特朗普在內外決策中的更大空間:他只會考慮三四成基本盤或關鍵盤選民的訴求,進而也就可以以「少數總統」的姿態做出更多前任難以承受的驚人之舉。
最近,無論是築牆、政府關門還是「緊急狀態」都是如此,但一旦在某一議題上獲得支持的規模低於了其基本盤的水位,特朗普就會當機立斷地快速止損:從接受妥協、結束關門到繞開行政機構、直接宣布737MAX停飛也都是這個邏輯,如出一轍。
在選民當中明確劃清界限、只固化自己的三四成選民的做法,當然是對難以改變的極化政治的最佳回應,但這種針對性固化極可能引發的是對手陣營的同步固化。於是,如果此時民主黨陣營剛好擁戴出一位在剩下六成多選民中製造充分動員的廣譜候選人的話,特朗普的「分眾國總統」就會因為太過「分眾」而難以為繼。
時勢造英雄,選舉看對手。特朗普到底是否具有「一屆總統相」,只有2020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才能最終給出標準答案。但在那個人浮出水面之前,甚至在2020年11月3日之前,全世界都應該做好特朗普「白宮第二季」的充分準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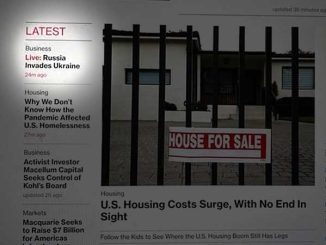
Be th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