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展靠理性,不靠激情,事實證明,「願景治國」「口號治國」是行不通的,要發展,就要尊重市場規律。
畢竟在這個世界上,殺頭的事有人肯幹,賠錢的事卻沒人肯幹。資本天然趨利,全球化的大門一旦打開,就很難再用政治把它關上。
一、逆全球化時代,中國需要開放4.0
自2019年以來,逆全球化的呼聲日漸嘹亮,在新冠疫情衝擊下,更成為焦點話題。
逆全球化暴露出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的短板:在現實層面,經濟與政治並未真正脫鉤,所謂市場自主、貿易自由,只是一個美麗的神話。
特別是在國際貿易領域,政治經濟學仍然佔統治地位。政治隨時可以伸出「看得見的手」,將競爭對手清剿出局。
由此帶來巨大的思想困境:在相當時期,國人奉自由主義經濟學為圭臬,而當這一思想方法與現實相乖離,我們該何去何從?
是徹底否定它,轉向民粹主義?還是深入思考,刷新並升級我們的認識力?
帶着這些疑問,去讀鄭永年先生的《貿易與理性》,會驚嘆於其中的通達、理性、平實。
在作者看來,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不論阻力多大,中國都應堅定信心、堅持理性,繼續站在風口上。
換言之,世界越封閉,中國就越應開放。
二、「中國道路」不是「美國道路」的克隆版
自特朗普上台以來,美國政府力推逆全球化,體現在三方面:
其一,退出多個國際組織。
其二,與中國等國家發起貿易戰。
其三,攪動民粹主義情緒。
在新冠疫情壓力下,美國政府更是加速了供應鏈「去中國化」操作,引起國內產業界的普遍焦慮。
焦慮的產生,源於這樣的誤會:
認為在過去40多年中,中國經濟是在重複「美國道路」,並因此取得快速增長,一旦失去美國背景,未來可能寸步難行。
在本書中,鄭永年先生指出:「中國道路」與「美國道路」並不相同,二者依據的是完全不同的政治經濟學。
在西方政治經濟學語境中,政治與經濟是一個分離的過程,這個過程至今影響着西方社會的方方面面。
在古希臘時代,西方的政治經濟學也認為政治、經濟不可分,與中國古人看法一致。
但羅馬帝國滅亡後,歐洲出現了數千個小王國,長期並存。在如何擴張上,商人們與國王們達成共識,政治與經濟從此展開合作。其結果是,經濟與政治脫鉤,取得獨立地位。
為強化此地位,資本進而贊同「保護社會」,使社會、政府相互制衡。
其結果是:政府與發展分離,政治人物想推動發展,也無有效辦法。隨着經濟的重要性不斷提升,政府日漸被邊緣化。
全球化後,資本實力陡增,貧富兩極分化加速,引發社會衝突。可從「佔領華爾街」,到「BLM運動」,西方政府始終拿不出有效的解決方案。
可見,「美國問題」是「美國道路」內生的困境,是西方政治經濟學的必然結果。
相比之下,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的經濟一直未獲得獨立地位,它始終呈現為三層資本共存的結構,即:
頂層永遠是國家資本,中層是國家與社會的結合,底層才是自由的民間資本。
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三層市場。
這種結構的缺點是,中國錯過了大分流的機遇,未能率先實現近代化,但它也有優點——最大化地保證發展。
在中國政治經濟學語境下,發展始終是政府的重要責任之一。
正如古代中國最優秀的政治經濟學著作《管子》,它不談「供需」,只談「輕重」。「供需」的主體是市場,而「輕重」的主體是政府。
三、推倒重來是不負責任的想法
沿着兩種不同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就能解釋:為什麼在過去40多年中,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如此之快,卻沒有爆發重大經濟危機;
以及,為什麼中國能快速完成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能大規模有效扶貧等。
任何快速發展的經濟體,都會受到陣發性經濟危機的衝擊,可「二戰」後,許多東亞國家和地區都實現了長期的、持續的增長,奇迹的達成,與儒家文化堅信「政府有義務推動經濟發展」有關。
不否認,中國政治經濟學也有自身的困境。
比如:怎樣在三層市場中實現平等,使所有企業能享受同樣的權利,從而保護好中小企業的創新能力。
再如,如何避免國家資本獨大,三層變成一層,在歷史上,王莽時期、王安石新政時期、朱元璋時期、改革開放前時期,都出現了這樣的局面,反而給經濟發展帶來傷害。
然而,一定要將中國政治經濟學歸併到西方經濟學脈絡上,要求它做出根本性改變,將經濟與政治剝離開來,則既無可能,也無必要,還會付出慘重代價。
更重要的是,這並不符合中國社會的實際需求,無法得到人民的支持。
任何系統都是優劣並存,從沒有一個系統能適應所有時代、所有國家。這就要面對真問題,逐步修正,而非不負責任地推倒重來。
現實的問題是,西方政治經濟學對中國政治經濟學存有巨大誤會。
從政治與經濟分離的視角看,中國政府致力於發展經濟,常被誤讀成強化自身實力,對其他國家構成了威脅,必須加以遏制。
四、虛構出來的「中國威脅」
特朗普政府反覆強調「中國威脅」,卻刻意忽略了幾個問題:
首先,在政治主張層面,中國與美國沒有根本衝突。
其次,在政治操作層面,中國對美並無威脅。
其三,中國政府對美國內部事務毫無興趣,也未挑戰美國的全球地位。
換言之,中美矛盾的實質是經濟衝突,不是政治衝突,把它升格為政治問題,不僅解決不了問題,還可能激化矛盾。
其實,早在2008年,美國政府便明確提出「逆全球化」主張,採取「製造業迴流」戰略,可從結果看,2008年,美國製造業在GDP中尚佔15%左右,到2019年,反而下滑到11%。
發展靠理性,不靠激情,事實證明,「願景治國」「口號治國」是行不通的,要發展,就要尊重市場規律。畢竟在這個世界上,殺頭的事有人肯幹,賠錢的事卻沒人肯幹。
資本天然趨利,全球化的大門一旦打開,就很難再用政治把它關上,在全球化時代,誰是效率的窪地,誰就會被淘汰,特朗普政府寄望於「效率不足政治補」,未必明知。
但在書中,鄭永年也明確指出,應正視西方政治經濟學的優點,即:強烈的現實感、憂患意識和競爭意識。
事實是,中國不僅在政治上對美國毫無威脅,在經濟上對美國也毫無威脅。美國最不可能,也最不應該與中國發生貿易戰。
可西方政治經濟學天然帶有競爭基因,它開放卻不包容,不允許任何一點威脅存在,這與中國政治經濟學更多關注內部完全不同。
在高競爭時代,如何提高敏感度,如何磨鍊主動競爭、主動出擊的意識,是一個值得長期關注的議題。
五、「以暴制暴」是最壞的方法
面對特朗普政府咄咄逼人的操作,該如何應對?
最壞的方法是:以暴制暴,不自覺地接受對方塑造,結果很可能從經濟糾紛,真的升格為政治糾紛,落入對方設下的詛咒中。
在歷史上,「一戰」前的德國便犯了這種錯誤,給國家、人民帶來深重災難。
面對民粹主義的挑戰,決不能用民粹主義回擊。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論是主動的民粹主義,還是應激的民粹主義,都是反歷史、反文明的力量。
旁觀者不會具體分辨,誰的民粹主義只是一種策略,大家只會指責弱勢一方,並將其污名化。這種污名化最終會變成施暴的借口。
這意味着,鬥智鬥勇不鬥氣才是正確的應對之道。不論對手如何挑釁,如何反智,中國政治經濟學都應表達出其理性、客制、利他的一面。
在書中,鄭永年先生提出了一個概念,即「單邊開放」。就是說,不論對方是否開放,我始終保持開放。
翻開歷史,英帝國以如此狹窄的國土、如此少的國民,竟一度佔據人類居住面積的1/4,成為第二個「日不落帝國」,其成功的關鍵就在「單邊開放」。它幫助英帝國戰勝了一個又一個對手,長時間維持了全球霸主的地位。
美國在「二戰」後成為全球霸主,但70多年來,其地位多次遭到挑戰,這恰好證明,不懂「單邊開放」,將事倍功半,加大成本。
從中國歷史看,朝貢體制其實就是一種「單邊開放」體制,從整體看,它維持了東亞世界上千年的穩定,堪稱國際關係中的一個奇迹。
這啟迪着今天的中國,堅定去走開放4.0之路——將資本、產能和基礎設施建設技術等優勢帶向國際,通過互惠,超越西方政治經濟學的利益陷阱、地緣政治競爭的狹隘語境,這才是應對逆全球化的最佳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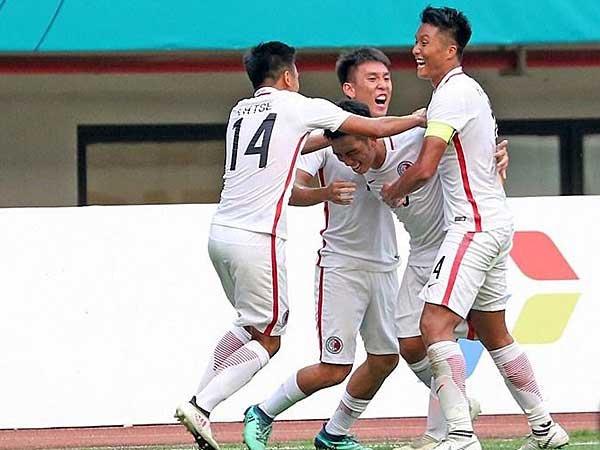
Be th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