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從2023年3月沙伊復交尤其是10月的中東打以之後,但凡伊朗有點風吹草動,網上就會冒出大量關於伊朗立場不堅定的議論,有的話還說得特別難聽。
尤其是在最近,萊西墜機、伊朗選擇低調處理,總統大選、改革派爆冷上台,特別是伊朗最高宗教領袖哈梅內伊向外界釋放了與西方國家緩和關係的信息,更是引發了自媒體的陣陣驚呼:伊朗慫了,要向猶撒妥協了!
代表哈梅內伊向外放話的,乃是伊朗外交關係戰略委員會主席、最高領袖外交顧問、前外交部長卡邁勒·哈拉齊,權威性沒問題。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哈拉齊職務的重要性,簡單類比,大致相當於咱們的中央外辦主任。相較於伊朗外長,他才是伊朗外交政策真正的操盤手,因為他能直接影響哈梅內伊。
雖然哈拉齊將改善關係的前提條件設定為西方的主動讓步,但這只是一種政治話術。因為主動示好,本身就是一種示弱,難怪引發自媒體的熱議。
這種議論能夠大行其道,除了話題與時機的敏感性,另外還有兩個主要原因。
一是關心則亂。
在人人自媒體的行動互聯時代、在人均政治家的中國,一般民眾的政治意識和國際視野得到了極大的開闊,對於伊朗在中美博弈大棋盤中的份量,大家都有一定的理解,但又理解得不夠透徹。
尤其是在中美博弈的時代大背景下、在中東已經成為中美博弈戰略制高點的前提下,身居陋室、心懷天下的中國人關注伊朗,實在是太正常不過,否則自媒體也不會將這當成炒作熱點。
正因過於關心,對於伊朗的舉動,不管是高調反美還是緩和對美關係,大家都很容易做出負面的解讀:伊朗反美都是吹牛逼,伊朗親美才是真實心態。
尤其是在第二個原因的推動下——有人故意帶節奏。
二是暗流湧動。
大國博弈,在發動最終一擊之前,前面都是認知戰。
所以才有吊民伐罪;才有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才有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
這個道理,與猶撒國拿著洗衣粉發動戰爭是一樣。即便洗衣粉是假的,那也必須弄一管出來。
正因如此,現在的中美博弈,在進入熱戰之前,也必然是各種形態的認知戰,例如政治戰、輿論戰、外交戰。
而目前的中東,正是中美博弈的焦點,由沙伊復交到中東打以的攻守轉換,正是中美博弈攻守易勢的分水嶺,伊朗則是分水嶺上一個關鍵的山頭。
由於伊朗長期的反美立場,這個山頭,天然更傾向中國。
由於伊朗長期存在親美勢力,這個山頭,又存在倒向美國的可能。
因此,對於伊朗正常的外交動作,肯定有人故意把水搞混,以挑撥伊朗與反美反霸反猶撒陣營的關係,尤其是中伊關係、俄伊關係、沙伊關係。
講明白這兩點,估計大家的心能放回肚子裡一半。
接下來,看完下面的分析,估計大多數人就能夠把心安穩穩全部放回肚子裡去。
因為伊朗反美乃是趨勢,非人力所能扭轉。
在《中美博弈的策略大轉折:中俄伊大三角?不,中俄中大三角才是根本》一文中,關於伊朗在中美博弈、中美俄大三角博弈中的作用與地位,曾經做過系統的分析,並且得出了兩個重要結論。

一是伊朗的角色與地位很重要,但並沒有達到足以支撐中俄伊大三角的地步。
二是雖然伊朗內部一直存在著親美勢力,但伊朗卻不可能徹底倒向美國。
用過老秤的朋友應該知道,秤砣之所以能夠以小制大、控制秤的平衡,是因為可以在秤桿上自由移動。

就體量而言,伊朗根本無法與中俄匹敵。因此,如果伊朗想要獲得與中俄平起平坐的戰略影響力,與中俄構成穩定的大三角關係,就必須具備高度的戰略彈性,也即具備在秤桿上移動的空間。
而伊朗欠缺的,正是這一點:伊朗反美,是當前歷史階段必然的趨勢,伊朗「親美」,只是趨勢之中的波動。
既然伊朗注定是反美的,自然,他也就失去了戰略迴旋空間,進而失去了縱橫捭閔的底氣與價值。
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現在的中俄關係,是充滿了彈性與想像空間且獨一份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因為只有獨一份,才沒有具體的參考物,才能保留最大的戰略迴旋空間。
這也就是我們看到的,對於伊朗的政策搖擺,不管是中俄還是猶撒,似乎都不是太在意。因為大家都知道,伊朗所謂的搖擺,無非就是虛晃一槍。
這樣的策略佯動,除了引發自媒體的陣陣驚呼,注定換不來太大的實際利益。
接著說說為什麼伊朗注定要反美。
第一個方面,外部環境不允許。
客觀評價,當前的世界秩序,依然是猶撒國挾二戰之威所建立的。
因此,不管是伊朗還是中國、俄羅斯,我們身處的大環境,其最主要的決定因素,依然是猶撒。
而猶撒秉承的大陸制衡策略,決定了他必須在世界上任何一個熱點區域製造敵人。
這個敵人,在全球範圍內,曾經是蘇聯、後來是俄羅斯、現在則是中國。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看不透這層關係,因此,在美俄博弈的過程中,大毛陷入了嚴重的戰略被動,不但被休克療法搞得奄奄一息,還失去了歐洲方向幾乎所有的傳統勢力範圍,陷入了嚴重的戰略被動。
現在的中美博弈,那些依然對猶撒心存幻想、帶節奏試圖讓中國放鬆警惕的人,不是蠢到了極點、就是壞到了極點。
猶撒不會放過中國,就跟當年不會放過蘇聯、俄羅斯。
同理,在中東局部,猶撒指定的敵人,正是本文的主角伊朗。
猶撒控制中東,主要有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清除英法勢力。
這個階段,猶撒針對的敵人是英法兩大老牌殖民帝國,主要戰略目標是清除英法在中東的影響力,主要方法則是透過支持魷魚建國找到干涉中東的理由,再與蘇聯聯手,利用蘇伊士運河戰爭也即第二次中東戰爭,從英法手中接管了中東。
第二階段是美蘇爭霸。
作為美蘇爭霸最重要的分戰場,這個時候的中東,猶撒的主要敵人變成了蘇聯,主要方法則是發動魷魚國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代理人戰爭,通過後三次中東戰爭尤其是第三、四次中東戰爭,猶撒成功瓦解了蘇聯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聯盟,同時也在中東國家、穆斯林國家、阿拉伯國家內部製造了新的矛盾。
第三階段是試圖完全掌控中東。
蘇聯解體後,為了徹底掌控中東,猶撒又將俄羅斯與伊朗打造成了新的敵人。之所以要加上伊朗,是因為俄羅斯的影響力迅速下降,無法獨立承擔中東公敵的重任。
也就是說,在蘇聯解體之後的後冷戰時代,伊朗所代表的什葉派與沙烏地阿拉伯所代表的遜尼派之間的矛盾,才是猶撒控制中東的主要抓手,也是掩蓋中東國家、穆斯林國家、阿拉伯國家與魷魚國、猶撒國矛盾的道具。
可見,當不當猶撒的敵人,不是由伊朗決定的,而是由猶撒國的中東戰略、全球戰略決定的。
伊朗要恢復與猶撒的正常外交關係,只有兩種可能。
一是猶撒全球霸權崩潰,失去在中東的存在。
二是阿拉伯國家集體反美,猶撒為了維持在中東的存在,只能反過來拉攏伊朗。
顯然,如果出現第一種情況,伊朗完全沒必要再去討好猶撒。
即便出現第二種情況,伊朗投靠猶撒的可能性也很小。
因為阿拉伯國家集體反美,說明中美博弈已經接近尾聲,猶撒國馬上就會落敗。
在這樣的情況下,反美幾十年的伊朗反投猶撒,即便他們的戰略決策層真的如此無腦,在短期之內,也難以扭轉巨大的政策慣性、輿論慣性。
這涉及到伊朗注定反美的第二個決定性因素,內部環境制約。
人們常說,距離產生美,這山望著那山高。
這是人性的弱點,也是人性的規律,而國家也是由一個活生生的人組成,因此國家的行為邏輯,也會符合人性的特徵。
對於猶撒,伊朗就是這麼一種心態。
巴列維時期,美國與伊朗關係很親密,但同樣產生了嚴重的齟齬。

在國家決策層,巴列維為了維持統治階層的奢華生活,同時也是為了發展國家、緩解內部矛盾,深度參與了前兩次石油危機,給美國經濟造成了沉重打擊,甚至影響到了美蘇爭霸的大局。
尤其是第二次石油危機,巴列維拒絕了美國人關於石油增產的建議,直接打了猶撒的臉。
因此,猶撒才把注意力放到流亡在外的霍梅尼身上,間接推動了伊朗伊斯蘭革命。包括革命爆發後,猶撒有無數種方法解救巴列維政權,但他們都選擇了拒絕。
但歷史總是充滿了迴力鏢,伊斯蘭革命的火,最後燒到了始作俑者身上。
那些同時受到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和傳統宗教思想影響的大學生,不僅把革命的矛頭指向了貪腐的巴列維王朝,也指向了曾經與巴列維沆瀣一氣的猶撒,進而爆發了著名的德黑蘭美國大使館人質事件。

人質事件爆發後,伊朗局勢徹底失控,霍梅尼也只能順從民意,高高舉起反美的大旗,猶撒也只能自認倒霉,放棄了這個中東地區最重要的盟友,轉而全力扶持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等阿拉伯國家,後來更是順水推舟將伊朗打造成了中東最大的敵人。

繼續說伊朗內部。
伊斯蘭革命最熱情的支持群體、衝入美國大使館綁架人質的,正是受到良好西式教育的大學生,也即所謂的精英階層。
而伊朗此後的政策搖擺,主要出在菁英階層身上。
一方面,這些菁英見識過西方制度帶來的經濟活力、也體會過現代文明生活方式,尤其是伊斯蘭革命之後,伊朗與西方國家之間形成了巨大意識形態鴻溝與經濟鴻溝,更是讓他們把西方體制當成了錯過的初戀,多美好有多美好。
另一方面,菁英們又要面對宗教人士與底層虔誠宗教信眾的雙重壓力,在內部改革上並不敢走得太遠。
而身為伊朗最高宗教領袖的霍梅尼與哈梅內伊,不管內心如何想,但在操作層面,卻不得不在兩者之間搞平衡:為了穩固神權統治,必須堅持反美的天然政治正確;為了保證社會的基本發展,又必須堅持適度的現代文明。
這種平衡,都集中反映在伊朗歷任總統的政治傾向。
伊斯蘭革命之後,伊朗產生的總統,始終在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搖擺,包括同一位總統,也經常出現個人政見的轉變。
有人認為,這是伊朗內部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但這更像是同一派系的政策調整。
簡言之,就是需要與西方國家緩和關係發展經濟時,就會推出改革派總統,需要與猶撒對抗時,保守派總統又會應運而生。
明白了這個邏輯,也就能夠理解,為何萊希墜機後,伊朗會低調處理,為何總統補選,改革派會重新上台。
因為前期的中東打以,伊朗已經掀起了反以反美的高潮,並且危及了猶撒的霸權根基。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伊朗不想變成猶撒垂死反撲的陪葬對象,就必然要做出戰術調整──換一個相對溫和的總統上台,緩和一下與猶撒國的關係。
因此,別說民眾選出了改革派總統,即便保守派繼續當選,伊朗的對美政策也會適當回收。
這種節奏變化,是大國博弈的常態,只要趨勢沒有改變,真沒必要大驚小怪。
此外,決定伊朗政局走向的,還有一個容易被忽視的約束條件──宗教,說具體點,則是什葉派與遜尼派的矛盾。
自公元七世紀阿拉伯帝國和伊斯蘭教同時崛起後,在遜尼派和阿拉伯民族的汪洋大海中,伊朗能夠作為民族國家生存下來,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選擇了小宗的什葉派。

這既是一種堅持,也是一種妥協。
另一方面,波斯人皈依了伊斯蘭教,也避免了最極端的宗教戰爭,雖然文化層面被伊斯蘭教大幅改造,但在生物基因層面卻艱難地苟了下來。
在人類文明史上,四戰之地的中東,曾經誕生無數大帝國、曾經生活過無數民族,但到今天,中東的主要民族,卻只有阿拉伯、土耳其、波斯、庫德等少數幾個。

其他民族,要不被消滅、要不被同化。
波斯民族綿延至今,本身就是生存智慧的展現。對於這樣古老的民族,我們應該保持基本的敬重。
他們的慫,與我們在特定歷史階段的韜光養晦一樣,只是生存策略,而非民族精神。
從歷史到今天,對伊朗來說,皈依伊斯蘭的同時選擇什葉派,從來不是因為慫,也從來不是什麼宗教信仰問題,而是民族生存策略。
這個策略,今天依然有效,尤其是對現代的伊朗。
這個策略,也必須做出調整,因為今天的歷史條件已經改變:在意識形態領域,伊朗不僅要面對遜尼派的衝擊,更要面對現代文明的衝擊、猶撒霸權的衝擊。
伊斯蘭革命之後,伊朗總統職位始終在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輪替,正是對這兩個方向衝擊的回應。
守住什葉派信仰,才能抵禦遜尼派的滲透,才能抵禦現代文明的影響,才能抵禦西方意識形態的輸入;適度擁抱現代文明,才能保證最基本的國計民生,才能維持最基本的軍工體系,才能抵禦猶撒的軍事威脅,才能在戰亂不斷的中東擁有自保之力。
而要守住什葉派信仰,就必須反美,因為佔據伊朗絕大多數人口的底層宗教信眾,包括伊朗好不容易張羅起來的什葉派抵抗之弧,天然就是反美的。
但要擁抱現代文明,又必須適度緩和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關係。
歸納一下,就是對伊朗來說,生存才是第一位的,發展只能退居其次;但就短期而言,又必須維持發展,才能確保生存。
為了生存,伊朗不得不反美;為了發展,伊朗又不得不「親美」。
堅持反美的同時適度「親美」,就跟歷史上一邊皈依伊斯蘭一邊選擇什葉派信仰一樣,同樣屬於波斯民族生存策略的一部分。
如果伊朗反美到底不做任何妥協,就會被西方國家長期孤立,最終導致國民經濟崩潰、政權崩潰。
如果伊朗真的投靠美國,就會失去立國根基,就會眾叛親離,就會變成中東公敵。
或者說,對伊朗而言,反美是道、親美是術,反美是戰略方向、親美是戰術選擇,反美是立國根本、親美是階段妥協。
道與術的關係,就好比太極中的陰陽轉換
對立統一的矛盾關係,在伊朗與猶撒的關係上所體現的淋漓盡致。
這種看似自相矛盾、實則自成邏輯的策略,就是波斯版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差別在於,經過二百餘年的摸索,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基礎上,我們逐漸開創出根植於中華文明之上、融合了馬克思主義和西方現代工業文明的獨立自主、改革開放之路,推動了中華文明的復興;伊朗在什葉派信仰之上,不管是反美還是親美,都很難發展出真正的現代文明,尤其是當他們的精英階層總是將發展的希望放在西方之時。
還是那句話,宗教世俗化,奠定了中華文明自信、開放、包容的文化基因,這也是老祖宗留給我們最珍貴的禮物。
未能實現宗教世俗化的伊朗,包括其他中東國家,要真正擁抱現代文明,仍會有一個艱難的自我革命過程。
從這個角度看,雖然同為古老文明,但我們已經領先波斯一步:我們現在追求的,不是最基本的生存權,而是最高水準的發展權;伊朗現在追求的,依然是最基本的生存權。
因此,某些自媒體對伊朗的嘲笑,校尉覺得很不道德。因為百年前的我們,不管做出怎樣的生存努力,也是這樣被所謂的西方文明嘲諷。
結語:
在歷史發文中,校尉曾經無數次強調沙伊復交的偉大歷史意義:
沙伊復交,大幅緩和了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宗教矛盾,也就緩和了中東內部的國家衝突、民族矛盾和領土糾紛,進而將反以反美的外部矛盾凸顯出來,為中東反美大團結奠定了輿論基礎。而中東反美大團結,又是架構世界反美反霸反猶撒統一戰線的關鍵環節。
同時,校尉不得不承認,從伊朗的視角看,從成百上千年的歷史維度來看,就跟反美大背景下的親美策略一樣,伊朗選擇沙伊和解,只是這個古老民族的階段性戰術調整。
對於沙伊復交,中國、沙烏地阿拉伯、伊朗的定位並不完全一致,尤其是伊朗
對伊朗來說,在處理伊美關係時,反美是道、親美是術,反美是戰略方向、親美是戰術選擇,反美是立國根本、親美是階段妥協;在處理什遜關係時,對立是道、緩和是術,對立是戰略方向、緩和是戰術選擇,對立是立國根本、緩和是階段妥協。
什葉派與遜尼派的矛盾,比伊朗與猶撒的矛盾悠久得多、複雜得多、深遠得多。
因此,在千禧年戰略層面,為了堅守自己的民族特性,為了確保自己的生存希望,伊朗必須高舉什葉派大旗。
這個與宗教世俗化、現代文明背道而馳的單行道,至少在目前,校尉看不到解決的希望。因為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宗教世俗化,而這正是伊斯蘭教的命門。
這種戰略困境決定了,當猶撒國被摧毀、當猶撒霸權崩塌之時,什葉派與遜尼派的矛盾,依然大概率會成為中東的主要矛盾。
當然,這是後人的難題。
我們這一代的歷史使命,就是在沙伊復交的基礎上推動中東民族大和解,在中東民族大和解的基礎上推動中東打以大聯合,在中東打以大聯合的基礎上推動中東反美大團結,在中東反美大團結的基礎上建構世界反美反霸反猶撒統一戰線,進而將猶撒霸權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至於如何在沒有猶撒霸權的世界中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包括如何消解伊斯蘭教的內部矛盾、以及催生內部矛盾的極端宗教思想,如何推廣宗教世俗化徹底改造現有宗教體系,實現從物質層面到精神層面的天下大同,進而帶領全人類開創輝煌的太空時代,那應該是我們下一代的歷史使命。
相信我們的下一代,會比我們更出色。
王陽明說,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校尉達不到王夫子的境界,只能說一句,心向光明、終無所畏懼!
在這個風起雲湧的大時代,讓我們始終堅持理想、讓我們坦然面對現實、讓我們勇敢迎接挑戰!
校尉相信,人類的明天會更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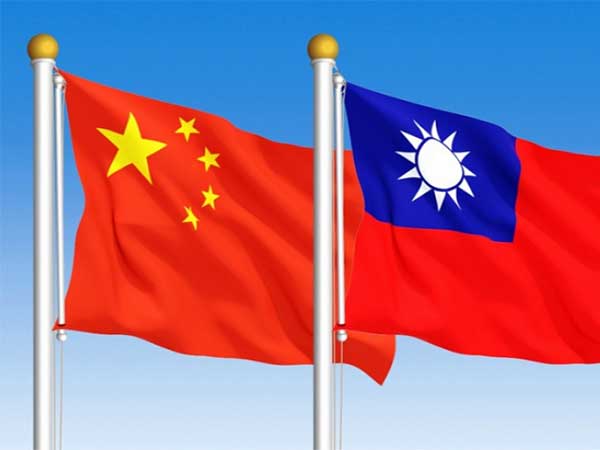


Be th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