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諾貝爾和平獎在5日揭曉,由兩名對抗性暴力人士共同獲得。他們分別是剛果婦科醫生慕克維格(Denis Mukwege)和曾遭伊斯蘭國(ISIS)禁錮、淪為性奴的雅茲迪族(Yazidi)人穆拉德(Nadia Murad),以表揚他們致力於中止性暴力行為變成戰爭或武裝衝突的武器。穆拉德為第17位獲此殊榮的女性。去年開始延燒的「#MeToo」運動浪潮,啟發全世界的人們重視性侵害、性騷擾問題,今年諾貝爾委員會選擇將全球關注的和平獎項頒發給打擊性暴力的人士,意義尤為重大。

慕克維格的獲獎恐怕難讓剛果國人同感榮耀。因為慕克維格的諾貝爾光環越是耀眼,照見的反倒是民主剛果的傷痛與不堪。慕克維格的國家經歷長年內戰,交戰各方竟以性暴力作為「武器」,讓許多無辜女性遭到性侵與殺害。慕克維格在前線設立醫院與中途之家,就是專門幫助這些受害者,自1999年以來已治療超過5萬名遭受性暴力的婦女,當中包含數以千計的第二次剛果戰爭中遭性侵的女性受害者。慕克維格奉獻自己的一生,保護戰爭受性暴力對待的受害者。曾接受慕克維格救治的數萬名女性,親暱地叫這位奇蹟醫生「老爸」(papa)。
剛果政府與盧安達胡圖族(Hutu)叛軍長年衝突不斷,除了武裝侵擾外,女性更淪為暴力性侵的犧牲品,戰士甚至迷信性侵女人可以獲得刀槍不入的力量,導致高達12%的剛果女性曾遭受性侵至少一次。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2014年的報告中指出,民主剛果有73%的成年女性與25%的女童曾經遭受性侵。《美國公共衛生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2011年也披露,根據2006至2007年間的調查,每天平均有1152名婦女遭到性侵,等於每小時就有48名女性遭到強暴,受害者年齡平均只有16歲,甚至連嬰孩都無法倖免。
身處悲慘的黑暗大陸中央,曾留學法國的醫師慕克維格不願獨善其身,也沒有離開自己的祖國,而是選擇直面問題,挺身營救被戰亂打入煉獄般人生的女性,除了醫療、安置她們,更協助遭到歧視與遺棄的這些女性重回社會。慕克維格也曾到聯合國呼籲「主持公義」、「儘速逮捕戰犯」,如此勇敢對抗軍閥的義行,也讓慕克維格幾乎命喪槍下,不過這位俠醫仍堅持跟剛果婦女站在一起。
慕克維格2014年就榮獲「沙卡洛夫人權獎」(Sakharov Prize),當初的得獎理由是「表彰他保護生命—尤其是保護婦女生命的不懈奮鬥」。慕克維格4年後再拿下諾貝爾和平獎,諾貝爾獎委員會則說他「致力終結使用性暴力作為戰爭武器的惡行,為保護性暴力的受害者奉獻一生」。
牧師之子,少年立志習醫
現年63歲的慕克維格,出生於剛果一個基督教五旬節派牧師家庭。他從小看父親為人禱告,由於剛果欠缺醫療資源,不少病患經過禱告自然也不見起色。年輕的慕克維格因此決定習醫,他在鄰國蒲隆地的醫學院畢業後,最初在南基伍省首府布卡武(Bukavu)的近郊擔任小兒科醫師,見到許多懷孕婦女因為缺乏照顧,死於難產或者產後傷勢惡化。於是他遠赴法國,在安茹大學(University of Angers)攻讀婦產專科。
從法國學成歸國後,慕克維格就碰上了1996年開始的第一次剛果戰爭。他一開始回到出國前的雷梅拉醫院(Lemera Hospital)服務,但是因為戰火頻仍,他只好搬到布卡武。不過慕克維格並未離開這個交戰熱點,1999年,他就在布卡武籌辦潘茲醫院(Panzi Hospital),原想為人接生、或者提供生產性廔管(obstetric fistula)等手術,降低婦女的難產死亡率。但是當醫院正式開張,慕克維格卻在這裡遇見了在戰爭中遭受性侵的第一個病人。
1994年,盧安達發生胡圖族人(Hutu)對圖西族人(Tutsi)的大屠殺,後來圖西族奪回政權,擔心被報復的胡圖族大舉流離異國。與盧安達相鄰的民主剛果,就是在此時迎來大量的胡圖族難民,但盧安達的武裝分子也趁此時進駐民主剛果東部。過去20年,民主剛果的政府軍與胡圖族叛軍衝突不斷,女性也淪為暴力性侵的犧牲品。慕克維格所在的南基伍省,恰好與盧安達國境接壤,加上南基伍省的礦產豐富,都是此地戰亂不絕的原因。
「性暴力根本被當成戰爭武器」
慕克維格說,這位病患的直腸、陰道當時被尖刀刺穿得血肉模糊,他十年行醫從未見過此等慘狀。隨著內戰持續,這類病患越來越多。慕克維格說,送到他醫院的受害者,經常來自交戰城鎮,而且全身赤裸、血肉模糊。在這個幾乎被現代世界遺忘的非洲大陸,慕克維格發現性暴力根本是被武裝團體當成「戰爭武器」,這讓他決定投身於受害婦女的保護與醫療工作。如今潘茲醫院已經收治超過8萬5千名病患,其中超過5萬人都是性暴力的受害者,經常伴隨嚴重的生殖器外傷。
「我見過刺刀的刀身沒入陰道、病患的外陰部遭到槍擊。有受害者在家人面前遭到性侵,甚至有受害者的家人被武裝分子強迫參與性侵。」
慕克維格有時得工作18個小時,一天要縫補十多個女性的陰部傷口,他也公認是治療性侵受害者外傷的專家。他所收治的病人多數無家可歸,她們被家族村落視為恥辱,有些人全家被殺光,也有人病重無法自理。慕克維格不只是醫治病人,更成立基金會,募款籌設中途之家,協助照顧、教育、安置這些女性受害者,提供她們心理諮商、為期12個月的識字與算術課。潘茲基金會甚至有微型貸款,還協助受害者對性侵者提告。
慕克維格知道,這些遭遇生命極大創痛的民主剛果女性,需要的不只是身體上的醫療。她們還需要心理上的陪伴,甚至社會系統的支持。他希望離開潘茲的病患,不僅僅肉體上的創傷痊癒了,從此也能在社會上勇敢自立。
慕克維格2012年9月曾赴聯合國人權調查委員會提供證詞,當時他說:「我很希望說,很榮幸代表自己的國家來到這裡,但是我沒辦法。我的心情非常沈重,真正讓我感到光榮的,是能跟勇敢的受害婦女站在一起,她們不管怎麼樣都堅強挺立。」「我們不需要更多的證據,必須儘速採取行動,逮捕那些違反人類罪的人,因為公義無可妥協!」
躲過死劫,卻抵不過病人呼喚
慕克維格的主張,讓他成為剛果武裝勢力的公敵,也幫自己與家人種下殺機。赴聯合國作證,再到歐洲演講返國後,5名持槍歹徒闖入他家,最後他的警衛被槍殺,慕克維格則奇蹟似地逃過死劫。在生命威脅下,慕克維格舉家遷往歐洲避難。但是布卡武的婦女都連署請願希望他回來,甚至賣水果蔬菜籌款幫他買機票。抵不過病人的呼喚,慕克維格在2013年1月14日返抵國門,《紐約時報》當時報導,許多剛果女性都到場迎接,「彷彿英雄歸來」。
慕克維格所經營的潘茲醫院如今有450個床位、370名醫護人員,其中250個床位保留給性侵受害者。由於不是每個病患都能支付醫藥費,潘茲醫院總是面臨經費與人員短缺。慕克維格對於性侵問題曾經表示:「由於(內戰連年)性侵在我們國家根本不會被追訴,性侵犯也認為他們可以為所欲為。」民主剛果政府2014年終於受理135名婦女提起的集體訴訟,起訴39名軍人,但判決結果僅有2人被定罪。慕克維格說:「如果性侵持續發生,沒有任何人受到制裁,那麼這一切的公義在哪裡?」
「她們終於被世人所知,我能看到她們有多高興」
在一點都沒有自由民主氣息的「民主剛果」,一直有傳言慕克維格會出來競選總統。由於民主剛果今年12月23日就要舉行總統大選,這項說法再度甚囂塵上,逼得慕克維格今年8月7日召開記者會自清。這位許多布卡武女性口中的「老爸」說:「我們國家還無法舉行一場自由、可信的和平選舉,我也不會參選總統。」
慕克維格對角逐大位沒有興趣,因為他的心始終掛念著遭到戰爭傷害的無辜女性。事實上,當慕克維格接到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他才剛開完當天第二檯手術。他說醫院裡的人開始騷動,有人還哭了,後來才搞清楚自己拿到諾貝爾獎。談到獲獎的感受,他還是心心念念他的病人:「我可以在許多女性的臉上看見她們有多高興,因為她們終於被世人所知,這真的非常感人。」
亞茲迪族女孩勇敢控訴伊斯蘭國暴行
同獲和平獎的穆拉德,本身也是性暴力受害者。她來自伊拉克北部的雅茲迪族群。2014年8月,伊斯蘭國在她居住的村落屠殺數百人,穆拉德與其他年輕女性,包括未成年女童,則被俘虜作性奴。被拘禁期間,穆拉德被重覆強姦及遭受其他暴力對待,並遭威脅指若她不加入伊斯蘭國,就會被處決。穆拉德逃離之後,向世人揭發伊斯蘭國屠殺亞茲迪族、以及販賣婦女兒童的暴行,並在國際間奔走呼籲國際刑事法庭能夠審理伊斯蘭國的戰爭罪行;穆拉德在2016年時也曾入選過諾貝爾和平獎,並著有專書《倖存的女孩:我被俘虜、以及逃離伊斯蘭國的日子》(The Last Girl: My Story of Captivity, and My Fight Against the Islamic State)。
諾貝爾委員會表示,穆拉德沒有屈服於要求性侵受害者噤聲的「社會常規」(social codes),而是展現無比勇氣,公開自己的遭遇,及為其他性暴力受害者發聲。
現年25歲的穆拉德·,來自伊拉克尼尼微省辛賈爾地區(Sinjar),是庫德族中的少數、亞茲迪教徒一份子。
當時仍是學生的她只有21歲,曾經夢想成為歷史老師,或是經營一家美容院。她說,在這場悲劇發生之前,她最喜歡參加克丘的傳統婚禮,幫自己的親戚朋友們打扮,「當時我預想的未來是和家人、社區團聚,畢業以後經營美容院。我和我的家人感情非常好。」
2014年8月的某日,在保衛家鄉的庫德族自由鬥士(Peshmerga)被擊退後,伊斯蘭國入侵了她的村莊,這一天,她親眼目睹六個哥哥和媽媽被處決,她則是被迫跟所有親人分離,送往他城,淪為奴隸。,伊斯蘭國佔據了辛賈爾地區,並開始了一場綁架、屠殺和奴役的慘劇,納迪亞的6個兄弟都死於這場屠殺中,而她與6千多名亞茲迪年輕女性則被當成奴隸,囚禁北部大城摩蘇爾(Mosul)。
她在自傳中寫下恐怖分子對她毫無人性的虐待。伊斯蘭國士兵將她和其他人送上巴士,送往其他地方販賣。士兵在車上對她們上下其手,將手伸進他們的衣服裡隨意搓揉,如果因為害怕而叫出聲就會換得一頓毒打,「跟伊斯蘭國共處的每一秒鐘都像緩慢痛苦的死刑─身體和靈魂之死。」伊斯蘭國士兵將她們當商品一樣販賣,要求他們打掃、洗衣、煮飯,並不分晝夜的強暴、毆打和囚禁。穆拉德曾試圖逃跑失敗,雖後便遭到三名士兵輪流性侵,直至昏厥。她在不同好戰分子手中轉送多次,想過自殺、毀容,最後只剩下徹底的絕望和麻痺。
在亞茲迪文化中,女性若與非亞茲迪教信徒發生關係後,就必須皈依伴侶的宗教。因此伊斯蘭國是藉由性侵亞茲迪女性,做為消滅亞茲迪族和信仰的武器。遭受性侵的亞茲迪女性承受的不只是身體的傷,也是從此與原生文化、社會分離的傷害。
逃離伊斯蘭國魔爪、遠赴德國重生
穆拉德很幸運地趁大門沒鎖、並找到鄰近村民大膽地將她「偷渡」出伊斯蘭國控制區,才輾轉逃亡到達霍克(Duhok)難民營。
「難民營的生活環境非常差,基礎物資不足,一天只有幾小時有電。我所待的難民營還算比較好的,其他的難民營狀況更糟,人們住在臨時搭建的帳篷裡,幾乎每周都會聽到有帳篷失火,一夕間所有個人物品全部消失的事情。冬天的時候還會淹大水,生活非常不安穩、令人害怕。」她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夠喚起國際社會對亞茲迪人的關注,「我們要的只是一個公道,還有還給我們安全無虞的家園。」
2015年2月,人在難民營的納迪亞首次接受《自由比利時》(La Libre Belgique)訪問,讓亞茲迪女性遭遇的慘況得以在國際曝光。
不久後、獲得德國巴登-符登堡邦政府的難民庇護資格,正式移居德國新家。同年12月,她出席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並為首位聯合國人口販賣倖存者尊嚴親善大使,為家鄉奔走和演講。
穆拉德曾在2016年,獲歐洲議會授予薩哈羅夫獎,表揚奉獻己力捍衛人權及思想自由。並得到巨星喬治克隆尼(George Clooney)妻子、英國知名律師艾瑪·阿拉穆丁(Amal Clooney)協助,對當年對她施暴的伊斯蘭國和其指揮官,提出屠殺、強暴、人口販賣的罪名起訴。
2017年6月,穆拉德在聯合國協助下回到家鄉克丘,卻是人事已非。她的家族成員18個人不是被殺就是失蹤。她在家鄉的土地上哭喊著「我是這個村莊出生的女兒」,她從未想過自己還能回家。當她在克丘與亞茲迪人見面時,久久說不出話,只是不斷的落淚。她感謝為她和族人奪回家園的戰士們,但也呼籲國際社會儘快還給她與族人一個公道「我們的家園被毀,超過1500名亞茲迪人還被俘虜、被虐待,過著慘無人道的日子。我希望至少歐洲和美國能多收容一些亞茲迪足的難民。」
性別平權終於邁步
今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反性暴力維權人士。長年以來被批評得獎者性別嚴重失衡的諾貝爾獎,經歷「#MeToo」反性侵運動,以及頒獎單位捲入性侵風暴以後,終於在性別平權上與時俱進,朝著打破男性主宰局面的方向邁開大步。
從多位女星出面指控好萊塢製片人韋恩斯坦長年性侵獸行開始,名為「#MeToo」的反性侵運動延燒全球最近剛滿1年。而逾百年來表揚各國傑出學者的諾貝爾獎,身為頒獎單位之一、地位崇高的瑞典學院,竟也在去年底捲入性侵指控,一名女院士的丈夫阿爾諾被控強暴與性侵,造成多名評審離職,終令瑞典學院今年停頒文學獎,創下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首例。
去年11月,受#MeToo運動啟發,18名女子指控法國攝影師尚.克勞德.阿爾諾(Jean-Claude Arnault)性侵和性騷擾,而阿爾諾正是瑞典學院前院士、作家嘉塔莉娜.費洛斯坦遜(Katarina Frostenson)的丈夫,與瑞典學院關係密切。當時,這樁醜聞引發學界對瑞典學院的不信任,引發瑞典學院院士的「辭職潮」,瑞典學院為終身職,但院士若拒絕出席會議,讓諾貝爾獎的評選工作停擺,幾乎等同辭職。當時辭職者包括費洛斯坦遜及瑞典學院常任秘書長莎拉.丹妮奧斯(Sara Danius),4月,瑞典學院三名院士也表態不再出席瑞典學院的會議。
今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剛果婦產科醫師穆克維格,以及曾淪為「伊斯蘭國」性奴的雅茲迪族女權運動家穆拉德。挪威諾貝爾委員會表明,這是為了表彰他們對抗戰爭和武裝衝突孳生的性暴力罪行。不少媒體5日紛紛用類似「向#MeToo運動致敬,諾貝爾和平獎表揚對抗性暴力」這樣的標題,報導和平獎揭曉的消息。
除了和平獎順應#MeToo潮流,今年諾貝爾其他獎項的性別比率也明顯改變,女性得獎者遠遠多於往年。已經揭曉的物理、化學與和平獎各有一名女性獲獎。相較之下,去年(2017)與前年(2016)的得獎者幾乎清一色為男性。
百年僅48女性得獎
諾貝爾獎歷屆得主性別嚴重失衡,一直是每年公布得獎者之際的外界關注焦點。從1901年開始頒發首屆諾貝爾獎開始,總共有892名得主榮獲桂冠,但百年來卻僅有48名女性得獎。其中30名女性集中於文學與和平獎,後來新增的經濟學獎僅1名女性得主。
就以物理學獎來說,百年僅3名女性得獎。雖然美國物理聯合會統計資料中顯示,物理學界全職教授僅10%是女性,但真正讓女性得主如此「稀缺」之因,則是學術成就或遴選機制的把關經常是掌握在少數男性教授之手。
去年諾貝爾獎揭曉後,諾貝爾獎基金會副主席漢森曾表示,「比較廣泛地說,有更多女性沒有獲獎,我們對此感到失望。我認為還有許多傑出女性應該成為獲獎候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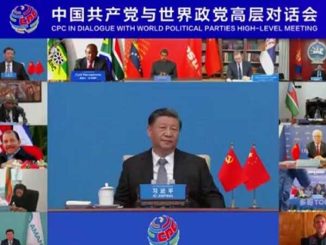


Be th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