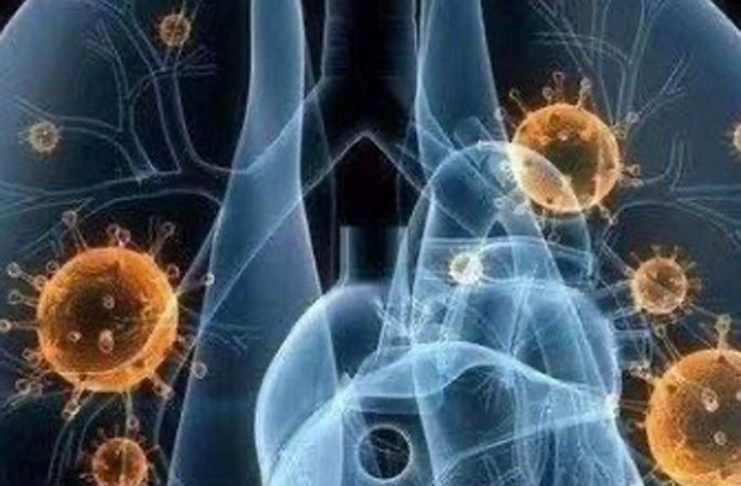
關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非常時期,需要冷靜、科學的分析,這篇文章非常值得關注。
這場疾病到底從何而來,源頭是什麼?
現在能夠確認的是,這次新冠病毒肺炎的幕後真兇就是一種剛剛發現的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
這已經是21世紀以來,冠狀病毒家族的成員第三次肆虐人類世界了。2003年和2012年,SARS病毒(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病毒)和MERS病毒(中東呼吸綜合征病毒)曾經兩次突然降臨人類世界,在中國和中東地區留下了至今尚未痊癒的傷疤。
我得提醒一句,確認任何一種全新傳染病的病原微生物都不是一件特別容易的事情。你可能直覺上覺得看看肺炎患者的肺部有什麼微生物就可以了,但是問題是在大多數時候一個人身體裡總是寄生着上千種不同的細菌和病毒等微生物,因此確定病原體的時候醫生和科學家們也需要非常小心才行。你可能還記憶猶新的一個反例,就是2003年SARS流行時曾經有科學家(中國疾控中心首席研究員,中國工程院院士洪濤)錯誤地將患者體內的某種衣原體判斷成了病原體,險些造成了疫情管理的大問題。
這已經是21世紀以來,冠狀病毒家族的成員第三次肆虐人類世界了。2003年和2012年,SARS病毒(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病毒)和MERS病毒(中東呼吸綜合征病毒)曾經兩次突然降臨人類世界,在中國和中東地區留下了至今尚未痊癒的傷疤。
我得提醒一句,確認任何一種全新傳染病的病原微生物都不是一件特別容易的事情。你可能直覺上覺得看看肺炎患者的肺部有什麼微生物就可以了,但是問題是在大多數時候一個人身體裡總是寄生着上千種不同的細菌和病毒等微生物,因此確定病原體的時候醫生和科學家們也需要非常小心才行。你可能還記憶猶新的一個反例,就是2003年SARS流行時曾經有科學家(中國疾控中心首席研究員,中國工程院院士洪濤)錯誤地將患者體內的某種衣原體判斷成了病原體,險些造成了疫情管理的大問題。
而如何判斷一種傳染病的病原體,其實有一個非常古老但行之有效的辦法:科赫法則。
這是德國細菌學家科赫在1884年提出的標準,用來判斷某種病原體和某個傳染病之間的因果關係:
每一個病患體內都能找到大量的這種病原體;
這種病原體可以從患者體內被分離出來,然後在體外培養;
體外培養的病原體可以讓健康人患病;
新患病的人體內仍然可以找到同樣的病原體。
在此後的一百多年裡,科赫法則也在持續地被修正過程中,但是總體而言仍然是整個科學界明確傳染病病原體的金標準。
具體到這次新冠病毒肺炎,中國科學家們在最早發病的幾十位患者體內,利用電子顯微鏡、RT-PCR和高通量DNA測序等方法檢測到了這種病毒的存在(科赫法則1)(Zhu N et al NEJM 2020;Huang C et al Lancet 2020);也成功分離出了這種病毒顆粒並且證明了它們在培養皿裡仍然能夠侵染人上皮細胞(科赫法則2)(Zhu N et al NEJM 2020)。當然,因為目前人們還沒有新冠病毒的動物模型。無法直接驗證科赫法則3和4,但是科學家們也證明了只要在老鼠細胞里轉入一個人類的ACE2蛋白——猜測中的新冠病毒受體,病毒就可以順利侵染這些老鼠細胞。這個結論至少是部分支持了科赫法則3和4的成立(Zhou P et al bioRxiv 2020)。
換句話說,在當下這個時間點,中國科學家們已經盡全部可能地證明了新冠病毒就是這種全新肺炎的病原體。
那接下來的問題是,這種病原體從何而來?
首先要明確的是,雖然同屬於冠狀病毒家族,但新冠病毒並非SARS或者它的變種,兩者之間的基因序列相似度只有80%,是相當遙遠的親戚(對比一下,人和猩猩的基因組相似度高達98%,人和人之間的相似度更是超過99.9%)。
人們已經獲得了新冠病毒的完整基因組序列信息(Wu F et al bioRxiv 2020),也有不少研究組已經把它和已知的許多冠狀病毒序列加以比對。其中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兩種天然寄生於蝙蝠身體內的冠狀病毒:一種存在於舟山地區的某種蝙蝠體內,序列相似度接近90%(Zhu N et al NEJM 2020);另一種則存在於雲南菊頭蝠體內,序列相似度高達96%(Zhou P et al bioRxiv 2020)。
而我們已經知道,同屬冠狀病毒家族的SARS和MERS的天然宿主很可能都是蝙蝠。蝙蝠這類哺乳動物體溫較高、免疫系統特殊,也是很多種危險病毒的天然宿主。從這個角度說,新冠病毒的天然宿主確實很可能也是蝙蝠。
但是我還是得提醒你注意:和確定一種傳染病的病原體一樣,確認病原體在自然界的天然宿主也一直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要求我們了解病毒從天然宿主到人傳播的全鏈條。這一點實際上SARS和MERS病毒都還沒有徹底證明。
其實比確認天然宿主更重要的,是確認新冠病毒的中間宿主——也就是找到它從蝙蝠到人之間的中間鏈條。要知道,雖然新冠病毒和雲南菊頭蝠體內的病毒高度相似,但是4%的差別其實也意味着蝙蝠體內的病毒是不太可能直接傳染人的。另外,新冠病毒肺炎患者體內的病毒樣本彼此之間基因序列高度一致,這本身也提示病毒應該是在某種中間宿主體內完成進化之後開始爆發的。
在SARS和MERS的案例里,科學家們確認果子狸和駱駝是兩種病毒最重要的中間宿主(Kan B et al J Virol 2005; Sabir JSM et al Science 2015),病毒在它們的種群內廣泛傳播和變異,最終變成了可以直接入侵人體導致疾病的病毒。那麼在新冠病毒的案例里,誰是可能的中間宿主呢?這個問題的回答對於我們日後防範新冠病毒捲土重來是至關重要的。
但是很遺憾的是,目前我們沒有很好的猜測方向。因為早期病例大多和武漢市內的華南海鮮市場有關,因此一個主流的猜測是也許那裡販賣的某種野生動物是病毒的中間宿主。但是遺憾的是科學家們沒有來得及在市場被封閉之前採集野生動物樣本,因此只來得及在市場的環境中進行檢測並確實發現了病毒。在這裡我可以給出一個粗糙的猜測:這種中間宿主應該是某種能夠較大規模飼養的半野生狀態的哺乳動物,這樣才能為病毒的突變積累提供時間;竹鼠、果子狸等動物是可能的尋找方向。在未來,規範和嚴打野生動物販賣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傳染病管控措施。
所以簡單總結一下,根據我們目前已知的信息,大概可以推測的病毒來源可能是這樣的:
某種寄生於蝙蝠體內的冠狀病毒因為某種原因進入了某種被人類大規模飼養的半野生哺乳動物體內;在那裡,病毒通過廣泛的互相傳播和突變,獲得了感染人類細胞並持續在人類個體之間傳播的能力;在2019年年末的某個時間點,它傳染進入了武漢一部分居民的體內並且導致了這場大規模的疾病爆發。
順便說一句,根據這些討論,你肯定能理解這種病毒大概率不是直接從野生蝙蝠傳給人的,實際上也沒有證據顯示華南海鮮市場里販賣蝙蝠,或者武漢居民對這種食物有特別的興趣。
當然這個簡單的推測還有不少問題無法回答。比如說,根據最新研究,新冠病毒肺炎最早的一位感染者本人其實並沒有華南海鮮市場的接觸經歷,最早的幾位患者當中也有不少人從來沒有去過這個市場(Huang C et al Lancet 2020),那麼他們到底是如何被感染的?是病毒在一開始就具備了人和人之間高效傳播的能力?還是說這種病毒另有傳染源頭?這些問題都仍然需要嚴肅的研究和回答。
衡量一種傳染病的影響,一個粗糙的思路是考慮兩個維度:毒力和傳播力。前者衡量的是如果一個人一旦患上該傳染病,癥狀的嚴重程度;後者衡量的是一個人有多大概率會得上這種疾病。
新冠病毒肺炎的毒力目前有一些粗糙的估計。在最初患病住院的40多人當中,病死率高達15%,重症監護的比例超過30%,都已經超過了SARS的水平(Huang C et al Lancet 2020)。但是如果綜合考慮更多癥狀輕微的患者的話,病死率目前在3%左右(大家可以利用隨時更新的數據自己計算),遠低於SARS(10%)和MERS(35%)的水平。而且考慮到大多數患者癥狀輕微甚至從未就醫或接受病毒檢測,一個合理的猜測可能是3%的病死率還是大大高估之下的數字。
而關於這種病毒的傳播力,有一個相對簡便的定量指標,叫基本傳染數(R0),代表在沒有外力干預的條件下,一個感染者平均而言能夠傳染給幾個人。可想而知,R0越大則意味着傳播力越強,如果R0小於1,則意味着這個疾病會慢慢自我消亡。作為對比,這裡列舉了幾個人類歷史上重要的傳染病的傳播力數據:麻疹(12-18),天花(3.5-7),流感(2-4),SARS(2-5)。
關於新冠病毒肺炎,目前則沒有比較好的估算數字。這一方面是因為疾病最初的發病數字很可能不太準確,一方面也是因為確診人數在快速的變動當中。世界衛生組織在1月23日給出過一個粗糙的估計在1.4-2.5之間,也就是說它的傳播力遠不如SARS。但同時也有一些研究認為新冠病毒的傳播力要比這個更強,甚至還有模型計算認為R0會在4左右(Read JM et al medRxiv 2020)甚至是5左右(Zhao S et al bioRxiv 2020)!在這個數據質量都比較粗糙的時候,我個人傾向於接受世界衛生組織的預測。
要知道R0數值的微小區別都會導致疾病感染人數幾倍甚至是幾十倍的變化,對R0的估計需要非常謹慎和全面才行,而這個數據也是傳染病防控需要掌握的核心信息之一。這方面,我們仍然需要來自一線科學家和醫生更多的數據!這方面的進展和披露似乎也還不夠迅速。
因此我在這裡只能給出一個比較粗糙和謹慎的猜測:新冠病毒的毒力遠不如SARS(但要顯著的強於流感),傳播力也應該不如SARS。因此,對於這場突發傳染病的解決,我保持高度樂觀。
這場疾病最終將如何被解決?
面對一種新型病毒導致的傳染病,大家的第一反應肯定是,「有沒有特效藥」,「有沒有疫苗」。希望能有好用的藥物來幫助我們殺滅病毒,能有疫苗能幫我們快速形成免疫力,防止病毒的侵襲。
在新聞裡確實能看到不少這方面的好消息,比如中科院上海藥物所和上海科技大學的科學家們聯手利用結構生物學輔助的化合物篩選平台,找到了三十種可能對新型冠狀病毒有效的化合物;再比如說中國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人員已經啟動了病毒疫苗的製備工作,疾控中心主任表態,「…疫苗是能開發出來的」。類似的新聞還有不少,這裡就不再列舉了。
中國科學家的這些努力當然值得讚賞,但是很遺憾的是,針對一種全新的病毒和一場爆發式的傳染病,特效藥和疫苗都很難成為我們期待中的救星。
這背後的道理其實不難理解,藥物開發也好,疫苗研製也好,從啟動研究到真正量產,就算一切順利,也仍然需要相當漫長的一段時間。而防控傳染病爆發的時間窗口遠沒有那麼長。說到底,遠水不解近渴。
我們拿SARS做個例子,這種嚴重的呼吸道傳染病2002年底在中國廣東爆發,在2003年夏季逐漸被控制。但是SARS病毒的疫苗一直到2004年春季才啟動人體試驗,2006年才正式完成,而到那個時候SARS已經銷聲匿跡,沒有大規模生產和接種疫苗的必要了。藥物開發就更是如此,至今人類也沒有真的開發出針對SARS的特效藥物,在實際治療中仍然以支持治療為主。所謂支持治療,就是通過輔助呼吸、抗感染、補充體液等方法維持患者的生存,然後等待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統消滅入侵的病毒。實際上針對大多數病毒引起的傳染病,人類都沒有非常好的特效藥物可以根除疾病。相關的例子還包括乙肝病毒引起的肝炎、流感病毒引起的流感、MERS和SARS病毒引起的呼吸道綜合征等等)。
17年前的SARS如此,面對剛剛突然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指望科學家們一夜之間拿出特效藥和疫苗來也是不現實的,誰拍胸口都沒有用。
當然,相比17年前的SARS,科學家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研究和理解要快的多、深入的多,而曾經針對SARS的研究經驗也提示了一些可能的方向。比如說上述中科院上海藥物所和上海科技大學的聯合研究就提示幾種針對愛滋病毒的老葯可能也對新型冠狀病毒有效,實際上不幸在前線感染病毒的北大第一醫院王廣發主任,自己就嘗試了一種名叫「洛匹那韋利托那韋」的愛滋病藥物,似乎也確實顯著緩解了病情。 這些線索當然有可能幫助我們找到能夠輔助新冠肺炎的藥物。還有,如今人類製備疫苗的速度也比十七年前有了很大的提高,甚至有研究機構計劃在幾個月內開展疫苗的臨床試驗(比如Moderna公司的RNA疫苗。RNA疫苗理論上確實可以有更快的生產周期。但是這種可能性僅僅還停留在理論上,至今沒有任何RNA疫苗已經完成人體臨床研究)。
但是無論如何,說在防疫急如星火的時間窗口裡,想要完成這些藥物和疫苗的研發、人體臨床驗證、大規模生產、配送和使用,真的不現實。
但我這麼說,當然不是說我們面對新冠肺炎就只好束手無策了。實際上應對這類突然爆發的傳染病,人類掌握了一種非常古老但是異常有效的辦法——那就是隔離。
隔離這個詞說起來通俗,但是背後的醫學原理是很深刻的。傳染病爆發的核心就在於它的傳染性:能夠從一個人直接或者間接的傳遞給另一個人或者更多的人。如果一個患上傳染病的人不能傳播給超過一個人的話,這種疾病自己就會慢慢消失。因此哪怕我們不掌握能夠直接殺滅病毒的藥物或者預防病毒的疫苗,只要能做到這一點——讓已經患病的人不能繼續傳播、讓還未患病的人不會被傳染——那我們就可以有效防控這種疾病。
隔離的核心有三條:
一是找到和管理傳染源。科學家們已經明確新冠病毒就是這次傳染病爆發的病原體,而且它可能在人與人之間傳播,那麼將已經患病或者疑似患病者快速識別出來並隔離治療,就起到了這個作用。
二是切斷傳播途徑。作為一種呼吸道病毒,新冠病毒的主要傳播途徑是通過飛沫傳播,但目前人們也無法完全排除其他的傳播途徑(比如接觸傳播等等)。因此切斷傳播途徑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避免人群的大規模的聚集和長距離的移動。
三是保護易感人群。面對這種新型病毒,可以說每個人都是易感人群(曾經有科學家貿然判斷兒童不是易感人群,這是非常危險和錯誤的判斷)。也就是說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做好自我防護,戴口罩、勤洗手、盡量不觸摸口鼻眼睛、減少出行、乃至鍛煉身體等等,都是在增加對我們自身的保護。
看到這裡,相信你就可以理解國家採取果斷措施對患者和密切接觸者實施醫學隔離,封鎖交通,取消公眾活動,號召大家戴口罩勤洗手的用意了。
我們甚至可以假設一個非常極端的情形:如果從今天開始全國人民都閉門自我隔離兩周時間(考慮到新冠病毒肺炎的最長潛伏期就在兩周左右),如果期間出現新冠病毒肺炎癥狀則迅速轉移至專門的醫療機構隔離和治療,那麼我們可以在兩周時間內徹底清除這種病毒的威脅。
當然了,這個極端情形是不可能真正實現的,畢竟整個社會仍然需要有序運轉,大量物資的流動在所難免、也有大量的人不可能完全居家不出,而對病毒的檢測也做不到如此的精準和高效。但是考慮到國家已經對傳染源密集的武漢等城市實施了強有力的管控措施,其他省市也在對輸出的病例也在做細緻的篩查和隔離,我對於能夠快速消除這種病毒的傳播還是非常有信心的。實際上,從1374年威尼斯封城對抗黑死病,到1910年伍連德切斷鐵路對抗東北大鼠疫,再到這次武漢封城各地嚴防死守對抗新冠病毒肺炎,隔離,始終是人類對抗烈性傳染病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在這場對抗傳染病的戰鬥中,中國科學家的表現如何?
簡單來說,中國科學家在這場戰鬥中表現極其優異;當然,也不是沒有可以商榷和改進的地方。
我們先說好的地方。
2019年12月初第一個病人因發燒和咳嗽就診,在此後一個月的時間內陸續有40多位類似癥狀的患者就診,12月底武漢市衛健委發布「不明原因肺炎」的警告。在一個月的時間裡,科學家和醫生們能夠發現一種全新類型的呼吸道傳染病的出現,這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速度。要知道冬季本來就是流感和其他呼吸道疾病高發的時間,武漢市內每天因為呼吸道癥狀就診的患者可能多達數千人,從中準確的發現一種與眾不同的疾病這本身就已經是很了不起的工作了。
接下來中國科學家的效率就更高了:在此之後,2020年1月7日,科學家們就已經確認新冠病毒是這次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體,1月10日完成了病毒基因組序列的檢測(Wu F et al BioRxiv 2020),1月24日嚴格證明了病毒的人傳人能力(Chan JFW et al Lancet 2020)。。這些工作為政府採取強有力措施防控疾病提供了科學指導。我們剛剛提到的中國科學家關於篩選藥物和製備疫苗的努力,也確實是非常有價值的工作。
從2003年面對SARS的混亂,到如今面對新冠病毒的快速和精準的反應,中國科學和中國科學家的進步是我們共同的驕傲。
但是我也仍然覺得有一些問題值得討論,甚至是批評:
比如說,我們看到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都發表於國際知名的學術期刊,比如《新英格蘭醫學雜誌》《柳葉刀》等。這固然是對這些研究質量的高度認可,但是考慮到傳染病防控工作的緊迫性,是不是真的有必要把發表論文當成重中之重的工作來完成?發表論文的過程(寫稿、審稿、修改等)是否會耽擱信息的共享?甚至我注意到,一部分論文需要付費訂閱才能獲取,這意味着中國其他科學家和疾病防控部門也不能自由獲取這些研究成果,展開下一步工作!面對兇險和急迫的防疫工作,中國科學家有沒有更快速、合理、廣泛的渠道公開自己的研究成果?我當然也注意到不少中國科學家選擇了bioRxiv等免費和公開的平台上傳自己的研究論文,這一點無疑是值得讚許的。其實說到底,科學研究的最高境界,不就是把成果寫在人類世界當中,寫在祖國的大地上麼?
再比如說,我也注意到在中國科學界內部,不少「跟風」「蹭熱點」式的論文扎堆出現。比如在病毒基因序列公布之後,數篇論文就迅速發表出來。它們的共同點是利用病毒序列進行了簡單的生物信息學分析,就做出了各種大膽的「猜測」,比如新冠病毒可能與SARS高度接近、可能寄生於蝙蝠體內,中間宿主可能是蛇、水貂等等(Xu X et al, 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 2020;Guo Q et al bioRxiv 2020;Ji W et al J Med Virol 2020)。這些猜測單就學術發表而言並無不妥,但很明顯缺乏嚴格的數據支持。我們當然要保障科學家的探索自由和發表自由,但是在防疫工作開始的初期,信息極度混亂和缺乏,任何可能的誤導,我想都是我們需要避免的。
還有,雖然在確認病原體的工作中中國科學家的速度驚人,但是至今公布的病毒基因序列信息仍然較為有限(26組數據),對於揭示病毒爆發的早期軌跡、分析病毒在人群中的進化趨勢,是遠遠不夠的。這方面的研究和數據共享仍然需要加強。而且我們還得注意,在研究工作紛紛開展的時候,各個研究機構和研究組能不能做到信息和研究成果的有效共享,會不會以鄰為壑獨佔數據,也都是我們需要提前警惕的問題。
接下來,中國科學家能做什麼?
我想,我們必須要吸取的一個教訓,是SARS平息之後,SARS相關的科研工作和藥物研發工作大部分都因為缺乏經費支持和市場前景停止了。考慮到新冠病毒入侵人體的路徑和SARS很相似,試想如果當年的很多研究堅持了下來,今天我們面對新冠病毒可能就會有更充裕的科學和醫學準備了。我們也許必須反思,我們整個科研系統對於傳染性疾病的重視程度是不是還遠遠不夠?
從更廣泛的角度說,新世紀一來,SARS、H5N1流感,H7N9流感,MERS、新冠病毒的連續出現和肆虐,其實本身就是對人類社會的一個高度警示。儘管我們建設了無以倫比的人類文明和高度發達的信息社會,但是非常原始的病毒生命仍然可能對人類世界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更重要的是,這些病毒的出現本身可能就是人類文明的高度發展的一個「產物」。伴隨着我們越來越多的入侵動植物的天然棲息地,越來越多的飼養家禽家畜滿足我們的生活需求,那些天然寄居於動物體內的微生物就獲得了越來越多的入侵人體的機會。而人類世界高度密集的群居環境、高度發達的人員和物資流動網絡,又給傳染病的肆虐提供了溫床。
比爾蓋茨曾經在一次演講中公開說,如果有什麼東西在未來幾十年裡可以殺掉上千萬人,最大可能是個某個高度傳染的病毒,因為我們在防止疫情的系統上卻投資很少,我們還沒有準備好預防一場大疫情的發生。
而這重擔會有相當一部分落在科學家的肩上。研究各種微生物的起源和進化,研究人類傳染病的傳播規律和數學模型,建立更精確的疾病預警和追蹤系統,開發藥物,製備疫苗,研究疾病的基礎生物學機理。。所有這些工作,都是我們的未來使命。




Be the first to comment